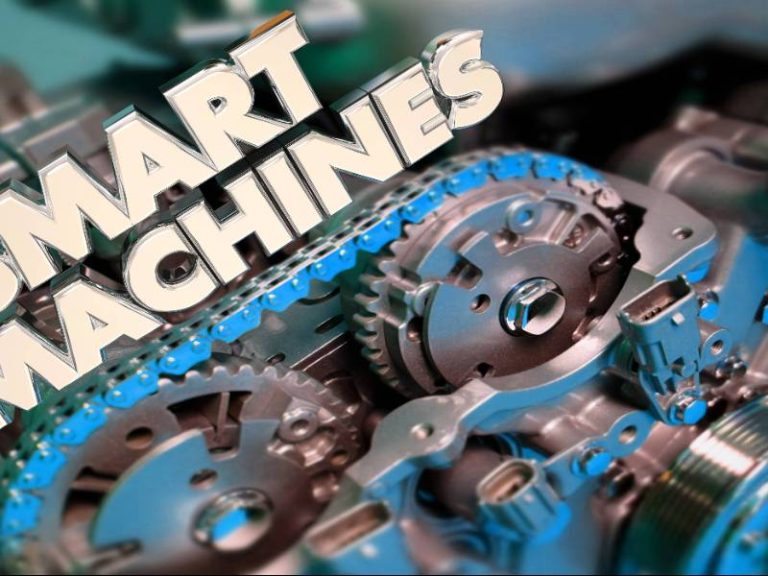【来源:虎嗅网】
近年来,在网络购药等政策的影响下,处方药在院外零售市场的规模占比逐年提升。参考米内网、中康CMH等几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2024年网售处方药的销售规模保守估计在350亿元~400亿元区间。
此前,处方药产品也已连续5年力压非处方药产品,在网售药品市场中市占率排名第一。结合医药电商当前的强劲增长态势,网售处方药的销售规模还将逐年增长。
要支撑起网售处方药市场强劲增长的势头,离不开互联网医院开出的电子处方的功劳。据《健闻咨询》访谈了解到,互联网处方价格近年来一路走低,如今已经维持在每张处方0.4~0.6元的平均市场价格。
在如此低廉的价格背后,是一条成熟的电子处方产业链。作为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医药电商平台(如美团、饿了么、阿里健康等),为了承接消费者巨大的寻医问药的需求,需要引入外部供应商来提供处方服务,而这些拥有互联网医院资质的开方公司,又需要招纳大量全职或者兼职医生来提供开方服务(主要以兼职医生为主)。医生在线上灵活接单,和滴滴打车的模式类似。
基于实际开出的处方量,医药电商平台会为外部供应商每张处方支付0.4元~0.8元的价格,而在产业链上作为外部供应商的开方公司,会为医生结算每张处方0.2元~0.4元不等的价格,具体的支付价格会根据医生的处方单量、在线时长、10秒开方率等多个指标来决定。
在各方的紧密配合下,这给消费者带来了网络购药的便利,也带来了过去几年来高速增长的医药电商市场。
但是,与实际的互联网问诊服务相比,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的开具速度与价格都有着明显不同。一个正常的线上问诊流程,医生需根据病人病情进行沟通、判断,费用往往在数十元(如百度健康、医联等对外的展示网络问诊价格皆在数十元不等),而补方开具的价格却低至几角钱。表面上,这是数字化带来的效率提升,但在“低价、高速”的背后,也伴随着一系列潜在风险。
中国的医药电商行业,如何行稳致远?
正常问诊要几十元,补方仅需几毛
在常见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上,一次线上问诊的价格通常在数十元不等,部分三甲医院名医的价格甚至超过百元,这和医药电商平台上每张电子处方仅几毛的价格过于悬殊。
低廉的价格带来了惊人的规模效应:头部平台年开方量已突破2000万张,全国累计电子处方量达到数亿级别,产业规模被业内估算已接近十亿元。
一张低至几角钱的电子处方到底是如何开具的?参与其中的平台、药店、互联网医院各方角色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为电子处方签名的医生又是如何参与其中?
《健闻咨询》了解到,在电子处方的产业链中,医药电商平台通常会集中向供应方集中采购电子处方服务,药店只需向电商平台缴纳年费,再为开具的每张处方支付少量审核费用,便可源源不断卖出处方药。
一位医药电商行业资深人士向《健闻咨询》透露,在某家B2C医药电商平台上,药店只需缴纳约800元年费即可接入互联网医院系统,每开一张处方再支付约0.6元处方审核费。
而第三方机构向医药电商平台端开出的价格,每张处方通常也只在0.4~0.8元之间。
如此便形成了消费者——药店——平台——互联网医院/第三方机构——医生的产业链条。
互联网医院依靠处方接口输出,医生完成形式化的“人工审核”,药店则借处方推动药品销售,平台在处方审核和药品交易两端同时抽成,最终形成闭环。可以说,从药店到平台,每一个环节都被嵌入了利益分成。
但医生并不是链条的必备环节,即便政策端目前仍旧严格禁止AI开方,“但现在大部分第三方机构全都是AI在辅助开方。”上述业内人士介绍,业内的头部互联网大厂们相对来讲还算比较规范,也就是使用AI进行辅助,再由医生进行最终的处方开具,但是一些为医药电商平台提供服务的第三方公司,为了降低成本甚至会使用自动开方。
作为链条终端的劳动提供者,医生能够从每张处方中分得的报酬也极为有限,一位曾在某头部互联网医院执业的医生透露,每开具一张处方他得到的报酬是0.4元。
开方过程也几乎全部由AI主导,“一张电子处方的审核至少需要一分钟,但在实际考核中,多数平台会要求医生在10秒内完成开方,医生根本来不及审核相应的风险内容,只能依靠AI的风险提示,再快速点击确认,和AI开方也没什么区别。”AI因此成了隐形的“处方师”。
但当处方成为处方流水线上的“快单”,风险也随之埋下。
部分药店和平台甚至会在处方时间上动手脚,将“先卖药、后补方”包装成合规流程。患者是否有过敏史、不良反应,往往由系统默认或由患者自行勾选,医生和平台则借此规避责任。
当前政策仍旧明确禁止的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也被药店与电商平台以这种方式规避。上述受访医生透露:“只要AI风控没提示,医生就不会细看,直接点确认。”
价格低、数量大、产业链紧密,使电子处方在现实中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高效的体系,但代价是安全性和合规性。
电子处方的真实运行机制,是当前政策监管与市场需求博弈的产物。而这种现实层面的“擦边”操作,其实与政策演进密切相关,要理解当下电子处方为何能如此运转,就必须弄清监管政策演变的脉络。
互联网处方政策的由来
截至今年7月,全国接入医保电子处方的机构突破35万家,累计开方量达6300万张。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静水深流的制度变革,从绝对禁止到试点破冰,从地方政策不一到全国通行,电子处方政策的每次迭代,都在重塑医疗市场的寻医购药生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互联网浪潮涌入中国时,上海第一医药网上商店的诞生曾点燃希望。但1999年《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流通管理暂行规定》的出台,直接将网络售药打入“冷宫”——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均被禁止在线交易。此后六年,医药电商在政策真空中沉寂。
转机出现在2005年,《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首次将医药电商牌照分为A/B/C三类,持C证的连锁药店获准销售非处方药,但处方药仍被排除在外。这道门缝虽窄,却催生了2006年第一张医药B2C牌照的发放。然而监管审慎始终如影随形,2016年,因“主体责任不清、处方药违规销售”等问题,国家食药监局叫停第三方平台试点,政策重新收紧。
直到2018年的拐点到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首次赋予电子处方合法地位:“允许线上开具常见病、慢性病处方,经药师审核后可委托第三方配送”。这份文件被业内视为“电子处方身份认证的起点”,它不仅承认了电子处方的法律效力,更首次提出医疗机构与零售药店处方信息共享的构想。
2021年行业出现了更大的突破,国务院《关于服务“六稳”“六保”进一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有关工作的意见》则彻底打开网售处方药的限制:“在确保电子处方来源真实可靠前提下,允许网售除特殊管理药品外的处方药”。至此,历时二十二年的网售处方药禁令宣告终结。
处方流转合法化只是第一步,医保结算的藩篱更高,由于各地医保系统技术标准不一,跨省处方流转长期受阻。2023年2月,国家医保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的通知》带来关键突破,允许定点零售药店开通门诊统筹服务,执行与基层医院相同的医保待遇。
文件发布后,政策效应迅速显现,全国零售终端处方药销售占比从2017年的16%升至2024年的21%。
对比不同阶段的政策文本,监管思路的演进清晰可见。1999~2017年间,以“堵”为主,通过负面清单控制风险,如禁止网售处方药;2018~2021年间,转向“疏堵结合”,在开放电子处方流转同时强化真实性审核,如2021年《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要求处方加密传输、留痕追溯;2022年后突出“技术治理”,2025年国标将安全要求细化到系统接口层面,用标准化实现可控开放。
监管重心的迁移同样显著。早期政策聚焦准入审批,如2005年ABC证分类,2022年《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则转向过程管控,压实平台处方审核责任;而2025年新国标更进一步,通过统一技术标准降低监管成本。
电子处方的低价、高效背后,是技术、市场与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几十元的问诊费用到几角钱的补方,数字化与规模化让市场活力空前,但也带来了合规风险和监管挑战。
可以预见,随着政策逐渐完善、医保结算体系日益联通,以及AI和互联网医院技术不断成熟,网售处方药市场将持续扩大。与此同时,如何平衡效率、成本与患者安全,将成为监管者和企业必须面对的长期课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健闻咨询 (ID:HealthInsightPro),作者:乔燕薇、庞贝贝,记者: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