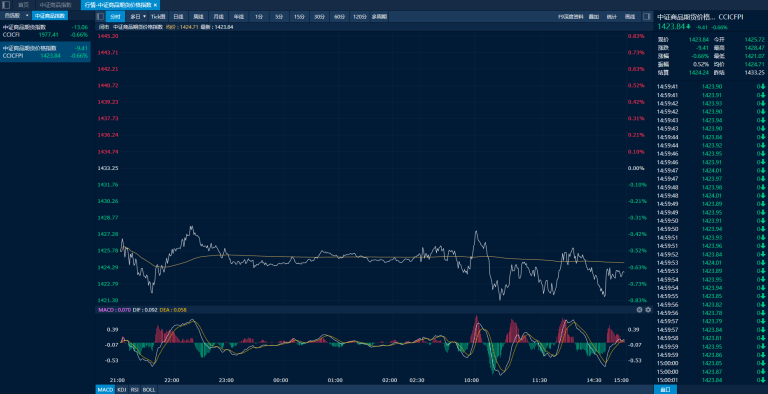【来源:虎嗅网】
最近两年,影视剧中的“虐女”成了摆在台面上的话题。在不少女性观众的反映下,从2024年开始,各大长剧平台播出的剧集中,虐女情节似乎大量消失了。像当年播出的《黑莲花攻略手册》、《春花焰》则完全摘除了虐女剧情。
而在另一种形式的影视剧——短剧中,虐女设定仍然占据主流。“虐女”是古早网文和电视剧的流行卖点,男主的利用和欺辱、女二的陷害是固定的创作范式。短剧作品中的虐女则着重刻画女性遭受暴力,尤其是性暴力虐待的场景,通过详细描绘女性的痛苦和屈辱,来满足某些观众的窥探欲望和感官刺激。
而这些虐女作品已经是一个个短剧女演员在行业到处碰壁可拍摄的最优选择。她们在虚构剧情中流血,在真实世界里失声。本篇文章主要讲述了“虐女”短剧从剧本创作到拍摄过程中,女性从业人员面对的各种困境与挣扎。
*触发警告:本篇内容会涉及有关女性身体伤害和性别暴力等内容的描写,有可能会引起创伤反应,请在自己状态良好、做好准备的前提下阅读,如果感到任何不适,也请及时退出阅读。
虐女是主流,爱女是谎言
短剧是时代的产物。
它的出现,契合了当下信息爆炸和生活节奏加快的社会现实,也迎合了观众们碎片化的观看习惯。短剧通常每集时长控制在1~10分钟之间,观众可以在通勤、午休或等候的空隙中快速浏览。短剧剧情紧凑、冲突强烈,以高度浓缩的剧情结构在短时间内快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带来强烈的“爽感”“甜感”或“复仇快感”等情绪情感冲击,给观众提供即时的心理满足,成为许多人用以缓解现实焦虑的情绪出口。
根据中信建投证券发布的公开报告,预计到2025年,中国短剧市场规模将超过650亿元,同比增长达36%。庞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大量资本与制作公司涌入,也催生了一个日夜运转的“内容工厂”生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今年第一季度,横店便接待了超过780个微短剧剧组,目前每天仍有近百个剧组在同时拍摄。
拍短剧不需要演技——开心就大笑,愤怒就皱眉,难过就落泪,不少没有学过表演的高校学生纷纷涉足短剧行业。
澄澄就是其中一员,她目前就读于杭州一所高校的文科专业,在2022年左右接触到短剧这一行,至今已经参与拍摄过近30个角色。在剧中,她常饰演那些外表温顺贴心、实则暗中算计、与女主构成对立面的女二或女三——在短剧语境中,这类“反派女性”形象通常被观众和行业归类为“白莲花”。她们往往以性别刻板印象为基础,既承载了对“伪善”女性的想象,也成为剧情推动中最易被消费的对象。
每一个想要入行的短剧女演员,“挨打”几乎是职业前期必须面对的一道关口。无论什么类型的短剧,女性角色挨打都是家常便饭,被视为推动剧情、调动观众情绪的“标配”。剧集前期,女主以受辱、受虐的形象出现,以激发观众的同情和愤怒;在剧情后段,暴力则转向女配角,通过“打脸”“教训”等手段来制造“复仇爽感”。这种暴力循环常常贯穿于上百集的剧集中,成为短剧工业中高度程式化、也高度性别化的叙事结构。
澄澄在拍摄第一部短剧时,就已对“挨打”有所预期。她被导演告知饰演女二号,“打戏”是最多的,但承诺“都是假打,不会真动手”。
但进入具体的拍摄环节后,她很快发现现实远比预期残酷。为了压缩成本,剧组请的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临演。她们缺乏基本的表演和镜头配合训练,几乎掌握不了“假打”的角度和节奏。澄澄回忆,有时候巴掌落下,她的脸转到了相反的方向,正挨上了巴掌。在导演“图省事、赶进度”的要求下,演员们也会被迫“真打”。
在一处租赁的别墅里,导演要拍摄多个挨打的角度,澄澄被扇了十来个巴掌,五次被踢,三次被浸入游泳池中。那天,为了完成一场被男主拖拽到泳池的戏,澄澄在拍摄过程中崴伤了脚,高跟鞋跟也裂开了个大口子。她匆匆换上备用鞋,无暇顾及崴脚的疼痛,咬牙坚持、抓紧时间完成下一条拍摄。
拍摄结束已经到第二天凌晨1点,澄澄细数那天的拍摄,总共拍了5场“打戏”,分别是扇巴掌、脚踢、浸水、皮鞭抽打、和捆绑威胁。即便知道这些都是在演戏,澄澄一天下来还是难受得盖着被子哭。
挨打并不单单是一种肉体上的疼痛,它更多是一种持续性的心理折磨。作为本能,任何生物都有保护自己身体不受外界伤害,人也一样。身体的挨打,却要求她抛弃这种本能,对心灵来说是一种非常直接的侵犯。
每次对手演员一抬胳膊,澄澄的心就咯噔一下,全身肌肉不自觉地收紧,发动潜意识不断自我催眠:“这是在拍戏,都是假的”。只有当镜头暂停,她的身体才得以松弛,心理才稍微缓解。
第一个项目杀青后,澄澄陷入了一种她至今都很难说清的状态。每晚睡觉前,她脑海都会闪回拍摄时被打的画面和经过,情绪也随之迅速陷入低落。
为了缓解这些不安的情绪,她会不停刷手机和播放熟悉的白噪音入睡,或者干脆用一些天马行空的幻想填满脑海,比如暴富和旅行。
澄澄在和 AI 软件 Deepseek 聊天时搜索:“为什么睡觉前总爱幻想”,Deepseek 告诉她,这可能是一种“解离性逃避”的应激反应——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在制度性暴力下的适应性病变。面对虚构伤害或真实威胁,大脑会溶解“自我”来保护有机体,通过幻想“美好事物”构建一个心理安全区。
这种状态只有脱离创伤环境后才能得到缓解。澄澄拍完第一部短剧后,一度萌生了退出短剧行业的意愿。但当她收到剧组财务打来的7000元片酬时,她的情绪“缓和”了许多,金钱有时确实能抚平一些心灵上的褶皱。
但她很快发现,和她一同进组、饰演男二号的同校男同学,片酬竟然和她是一样的。不过他只拍了3天,获得3000元。
这个片酬澄澄在进组前便知道,男女同酬,每天都是1000元。但在拍摄过程中,澄澄感觉自己和男同学的工作量明显不对等。她要负责挨打、浸水、捆绑这些“动作戏”,而男同学作为男二号仅仅需要在男主身边插科打诨,或者助攻男女主角的恋爱进程,最大的工作量就是给澄澄扮演的女二号两个耳光。
明显的“同酬不同工”是澄澄进入短剧行业的第一个疑惑,但行业规则如此。每个短剧剧组都是按天计酬,没有人会细算今天谁多挨了两个耳光、谁在水里泡了更久,这太麻烦了。
“女演员需要承担更多工作量”,既是剧本结构,也是行业逻辑:前期是女主角受尽欺辱和打压,后期则轮到女配角遭遇“反噬”,男演员只需要负责呈现荷尔蒙和传递性张力。
即便是同一场戏,男演员只需出场说几句台词,女演员却要挨一顿打,但最终仍被计为“同一工作量”,被支付相同的片酬。除非跻身头部,少数女演员才有机会协商剧本与待遇,大多数女演员都集体默认了这样不平等的存在。
随着澄澄进入更大规模的承制公司拍摄,剧组配置也逐渐“专业”起来。导演反复强调“假打”,要求避免破坏妆造——补妆耗时,而时间就是金钱。
在这样的剧组中,女演员们会自发地聚在一起讨论:什么样的角度和方式能让假打看起来更真实,以防过不了要多拍几次,被导演呲儿。
澄澄总结了一些“假打经验”,比如,扇耳光时最好依靠演员的面部表情来展现结实的“打击”;打的时候五指张开,可以分散受力;避免直接打击面部,改打到耳朵下方靠近脖颈的位置。
掐脖子戏份可以让对手演员将虎口贴合喉咙中央,拿拇指和食指两根手指轻轻发力,但不真正施压,如此可以实现画面张力的同时,保持呼吸与安全,也不易毁妆。至于拽头发或者衣服拖行的戏份,男演员需暗中发力托住女演员身体重心,避免对方穿高跟鞋时扭伤或摔倒。
有些假打经验来自于网络教学,更大一部分,是女演员在一次次拍摄时感受到的真实疼痛中共同摸索出来的。在缺乏正规表演训练、半数演员为“跨行转型”的短剧行业中,这套看不见的“行业知识”和“血泪教训”反映的是:当制度培训缺位、保护机制薄弱,女性只能依靠彼此的经验与身体,来学习如何在剧本规定的暴力中“优雅求生”。
澄澄把这些“假打”经验记录到自己的手机备忘录里,每进一个组都会在组群里给大家发一遍。有些人会觉得澄澄是多此一举,何况她只是一个普通演员,连女一号都没有演过。但澄澄的想法是她多发一遍,可能就会少一个女演员受伤。
男频擦边,不受保护的“现实凌辱”
在男频短剧中,虐待女性角色往往与强烈的性凝视紧密相关。这类作品中的“虐”,不再局限于身体暴力,而更常体现为各种形式的性暴力、性羞辱与边缘色情表达。
这些带有性暗示与性暴力色彩的桥段,往往带来极高的数据回报率、一位短剧制片人这样说:“之前有部擦边剧,投流500万回了快2000万,ROI(投资回报率)实在太高了,男观众就是比较吃这一套。”
在算法逻辑主导的平台环境中,这些指标直接影响内容的分发与商业价值,从而形成一种“性别暴力被商品化”的反馈循环。在这一机制中,这些性别暴力与羞辱的表达不仅成为叙事的看点,更被平台与制作方视作可精准计算与放大的“流量资产”。
短剧女演员雯雯现在不接演涉及擦边、凌辱情节的角色。她坦言,在一次饰演男频短剧的女二号的经历后,认为自己难以承受这样的对待。
男频短剧中,女性角色被严格类型化:女一号一般作为男主的官配,主要负责清纯白月光的情感投射,而女二号则承担情绪宣泄与欲望投射的功能——这类角色设定往往“恶毒”“性感”,融入擦边和凌辱的剧情中,满足男性观众隐秘的观看欲望。
业内所谓“擦边”女演员和“正常”女演员最大的区别是“身材好”、“放得开”。事实上,许多女演员在入行初期也是奔着拍摄正常剧情去的,但是现实的路径远比她们想得要窄。
雯雯的经历也是如此,当她去面见导演和制片人时,对方毫不掩饰对雯雯身体的大量,极力劝说雯雯尝试更“露骨”的角色,拍摄擦边剧情。
“我们是正规剧组,成片上红果和番茄大平台,肯定不能拍那些违规的剧情。动作戏都是借位,擦边程度咱们前期都会规定好,而且片酬也更高,你考虑考虑。”
这类涉及性暗示或羞辱性内容的擦边角色,往往在招募演员之前就会明码标价:摆特定的动作是多少、露胸是多少、露腿是多少,若涉及凌辱剧情,价格则更高。这类角色的片酬通常比同组其他演员高一到两倍。
“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短剧这一行片酬比较乱。”雯雯说,“会有一个大致的区间。看你能不能和导演、制片给自己争取高一点。”
最终,在制片人和导演的软磨硬泡下,雯雯接受了5000一天的拍摄报酬,决定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尝试一下原本抗拒的角色类型。
一个业内的共识是,女频重视男演员的颜值,男频则对女演员外貌提出更严苛要求。
尤其是男频短剧中的女二号,“擦边”角色的选拔标准严格且单一——肤白貌美、大长腿。定妆当天,雯雯被一一“展示”给剧组的男性工作人员确认形象,直到所有人点头认可,才被视为“适合男性用户观看”“能受到男性用户欢迎”。
然而,即便在拍摄前已对“尺度”达成共识,进入实拍环节后,导演、摄像、对手演员不断地向她施加语言压力:“打开点”、“再打开点”、“没事儿没事儿,你能放开点么”,试图再而三地逾越原本商定好的边界。
雯雯把裙子往大腿上一撩再撩,内裤都快露出来了,导演还是不满意。她直言,很多导演并不会骂你,但他用沉默来逼迫你屈服。
在短剧拍摄现场,每一秒都意味着金钱的消耗,进度被严格计算在剧组每个人的目光中——“大家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在这样的视觉压力下,雯雯只好选择妥协,把裙边又往上提了3厘米。
屈服的瞬间,雯雯心头泛起一阵委屈,明明是剧组人员不信守承诺,却像她是那个“犯错的人”。雯雯的情绪低落,但没有人在意。整个剧组都在赶拍摄进程,她不得不打起精神去准备下一场戏。
在当天拍摄结束后,雯雯和导演反映:希望后续能按照原先约定好的尺度拍摄,避免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导演口头上答应,但到第二天拍摄时,言语的压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冷峻、更难以抗拒的控制方式——沉默。
雯雯回忆那一幕时,感到自己在镜头面前竭尽全力、突破底线地搔首弄姿,摄像一个劲儿地在镜头后面叹气,导演双手交叉环抱在胸前,冷眼看着自己。整个剧组氛围降到了冰点,大家都在看导演的脸色,而他不说OK也不说继续,让气氛就这么尴尬着,只有雯雯一个人站在镜头前不知所措。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和剧中的女二号融为一体。角色在剧中被凌辱,而她在现实中又何尝不是。“接受不了大尺度就不要接啊,有病。”有人在人群中窃窃私语表达不满,音量正好被雯雯听到。
短剧的拍摄周期很短,一个剧组的成员匆匆而聚,四五天后又匆匆奔向下一个剧组。大家没什么感情,说话也很干脆。这样直白的话语让雯雯脑海中那根紧绷的弦瞬间崩断,她只能选择中途退出。
剧组迅速用比她高一倍的价格招来另一个女演员补拍她的露脸戏份,而那些露身体的其实用的还是雯雯拍摄的镜头。
“一旦女生成为擦边演员,就很难再回去拍摄常规剧情,相当于把路走窄了。”雯雯回忆,从那个剧组以后的一两个礼拜,后续面试的导演只要得知雯雯拍摄过擦边剧情,便会极力推荐她继续走这个方向。
大部分擦边女演员还是会一直选择拍摄擦边剧情,一是常规剧情不会被考虑;二是擦边女演员的高片酬与流量效应,构成了现实的吸引力。在拍摄机会极不稳定的短剧行业中,许多女演员更倾向于在有项目时尽可能获取更高回报,否则下个月就可能面临颗粒无收。
雯雯说:“可能是行业本身需要一部分女性干这种活儿,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地挤兑这部分女性继续走这条路,不然后面就找不到人了。这是我的个人看法,不一定准确。”
但更令人惊诧的是,有些预算较低的男频剧组,甚至会用“偷拍”作为手段,用常规剧情的名义拍摄女演员走光的画面,在剪辑中以擦边和软色情的方式完成分发,用更低的片酬制作出更高的流量回报。
雯雯的朋友孙捷曾遭遇类似情况。她在一部短剧中饰演女二号的随从,台词只有几句话,拍摄时间只有两天,日薪500元。按理说,这样的角色不应涉及擦边软色情的镜头——因为在行业里,“那是另外的价钱”。
但是在拍摄过程中,摄影师会用非常低的角度对准孙捷的裙底,几乎所有女生的裙底都被镜头不动声色地扫过。这让孙捷非常反感,她无法理解这些镜头的用途,更无法接受导演在场却视若无睹的沉默。
孙捷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被同样对待的女演员,大多数人的回应是:“算了,反正咱们穿着安全裤和光腿神器呢”。能理解其他女演员的顾虑,不同于她还在上学,其她女演员大部分是表演院校出身的全职演员,有的刚毕业不久。
王沁就是2024年毕业生里的一员。四年前,她以全省表演统考前三十的好成绩考进某传媒类高校。大学四年,她拍过银行和品牌的宣传片,也参演过微电影。但临近毕业,,她发现自己的行业路径越来越窄。班里32个同学,有25个左右都进入了短剧剧组。剩下的,有些是富二代,有的头铁去闯长剧,还有一两个“嫁人了”。
短剧成了唯一且现实的职业路径,王沁只能被推着走。至于像孙捷那样的情况,王沁从难受到习惯,现在甚至开始向摄像自嘲“我身材一般,别拍我了”。
“本来现在就是行业冰封期,你一个不注意落下‘小牌大耍’的名声,他们在导演和摄像群里随口说一声,就能堵死你的路。只能保护好自己,三角裤外穿安全裤再套一层肉色打底,像现在这样的天气站一会儿就全湿透了,但是没办法,吃的就是这碗饭啊。”
也有两个女演员选择和孙捷一起去质问那位摄影师,摄影师先是矢口否认,说拍摄角度是正常的。在要求查看当天的素材并提示小心被其她演员“避雷”后,摄影师又说,“不是故意拍的”“拍别的地方时不小心扫到了”,转头迅速开始删片。她们最终确认了确有裙底镜头后,要求删除,但摄影师只答复:“只能让后期剪辑操作。”
这部短剧上映后,孙捷把整部剧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她和跟一起反抗的两位女演员“走光”镜头至少被剪去了露脸的部分,至于是否仍然有身体暴露镜头,孙捷也无法辨认。
但是其他沉默的女演员并没有那么幸运,被放出了不少“走光”镜头。这些画面在互联网上无远弗届,至今依然在互联网上被传播、观看、消费。
从敏感到麻木,边界在哪里
剧本是短剧流水线工厂的第一道程序。作为内容生产的源头,编剧对于市场风向更为敏感。作为有两部上线短剧的编剧,宁惠今年提交的两部短剧初稿都被主编反馈“情绪不到位”。
宁惠写的是女频短剧,“情绪不到位”用大白话来讲就是“虐女程度”太低。
所谓“虐女程度”,是近几年短剧市场为争夺观众注意力而逐步建构出的情绪刺激标准。短剧行业经过三年的发展期,目前正在进入一个瓶颈阶段。观众的情绪阈值被拉高(情绪阈值,指的是一个人对外界刺激产生情绪反应的最低限度),简单的“虐女”已经无法让观众买单。
现在的短剧“虐女”手段要求更过分,如果剧本只是单纯的摁头入水、掐脖子、绑架、殴打这些手段,虐女程度就很低。
要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剧本需要构建更具冲击力的“身体叠加心理折磨”的“双重虐”场景。比如,女性角色在被殴打后流产(身体虐),紧接着听到相依为命的失明奶奶被人推下楼梯(心灵虐),这样的双重虐是现在短剧市场比较流行的呈现方式。只有当女性角色的痛苦被立体化地呈现,她们的“柔弱感”才能更彻底地激发观众的情绪。
甚至很多短剧的虐已经开始呈现一种“伪人感”,送监、割子宫、挖肾、抽血、得艾滋、打胎、活体器官移植……越来越多脱离现实伦理的情节被强硬植入剧本。这些剧情是否能过审、是否构成了需要被警惕的视觉暴力,似乎都不是剧本创作者需要考虑的事。
作为文字工作者,宁惠对于剧本写作保持高度的敏感。在一次撰写“女主被女配用钓鱼钩戳破十指吊着走”的剧情时,她一度出现肢体幻痛。更严重的时候,她会发生生理性的反胃,立刻跑到马桶边上呕吐。
她在编剧群中尝试分享自己的情况,一些比她入行早的编剧说:“正常,我之前也有这样的难受,写得多就不觉得有什么,这都是假的,咱们为了赚钱嘛。”
到最后,这些让宁惠消耗、反感的细节并没有被拍出来。如此“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情况很多,甚至有些返工二十余次的虐女剧本,会因为赶不上市场潮流被直接毙掉。但下一次,主编还是要求宁惠去写得再狠一点,“拍不拍出来是过审的问题,但虐一定要升级,哪怕是让演员口头表述,也能拉高观众的情绪。”
在这样的系统中,“虐女”剧情成为一种不断迭代的情绪技术,却不指向真实世界的反思。由于短剧不以教育人为目的,也不在剧中植入主流价值观,仅仅表达普通老百姓的情绪,赤裸裸地抒发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所以才能在下沉市场那么火爆。数据表示,这类内容的受众多数是四五线城市的女性。
宁惠说,生理上的不适还可以忍受,毕竟这是工作。但在意识层面,宁惠时常反思,她写的“虐女”剧情会不会给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女性观众、或者还尚未具备分辨能力的青少年用户带来负面影响。
虐女短剧中的性别叙事,往往将女性角色塑造成柔弱、无助、受控的形象,而男性角色则被描绘为强大、理性、有控制欲的“上位者”。这类大男主叙事不仅构建了性别刻板印象,也在潜移默化中干扰了女性观众对自我价值和关系模式的认知。
一项覆盖17,000多名青少年的纵向研究(COMPASS Study, 2023)发现:女性若每天观看3小时以上大男主叙事的影视作品,其抑郁风险显著上升(OR=1.30),这一影响在女性样本中尤为显著。
这类内容使她们更倾向于认同“情绪照顾是女性本分”的观念,也更容易形成“身体监控”行为——频繁照镜、担忧体重、控制饮食,标准化系数为.095-.141。
这意味着,在不断重复的情节中,女性观众被逐步训练成了“女主”,但并不会拥有属于她们的完整的叙事主线,而是一个“为他人牺牲”、“推动他人成长”的陪跑者。
在一些虐女剧情中,施虐者的暴力行为往往会被美化或者合理化,贴上“深情”“无奈”“病娇”等标签,这种模糊道德界限的呈现方式,有可能让部分观众对暴力行为产生情感错认,将其视作“爱的表达”,从而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和安全感知。
宁惠时常在网络上看到数起中学女生被霸凌、被剥衣拍摄的事件报道。在她看来,这些做法与短剧中频繁出现的羞辱、围观、身体暴力等情节如出一辙,是典型的“虐女手法”。据她观察,10部短剧中,大概有6部都会出现类似桥段,不是羞辱女主,就是打压“心机女配”。在某些下沉平台与二次剪辑中,这些桥段被反复传播、剪成爽点视频,成为青少年观众的模仿模板,甚至会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去实行。
这并不是在将短剧简单地等同于社会霸凌和校园暴力,而是揭示出一种文化氛围的共谋——当女性被持续以痛苦、羞辱和牺牲的面貌呈现,她们的受难就有了合法化的审美语境,而模仿者也就拥有了施加暴力的心理“动员机制”。
宁惠问在上中学的外甥女,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外甥女脱口而出:“那肯定是这个女生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让宁惠陷入不安。
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即便这个女生做了过分的事,也不该被这样羞辱和伤害”。但她很清楚,在外甥女看的甜宠短剧里,惩罚女性的桥段就是这么做的,甚至宁惠也写过很多类似剧情。
更可怕的是,宁惠也真实地从虐女剧情中获得过爽感。在一次写完女配被虐的剧情后,宁惠竟自然而然地开始审视自己的剧情设置是“真爽啊”还是“不够爽、还应该再狠一点”。在脑子里冒出这个想法的那一刻,她被自己吓住了。
宁惠只能劝慰自己,这只是站在编剧的角度,评估剧本作品的市场表现,而不是真的代表她认可这样的剧情。但她也明白,这种思维的偏移,正是思想上慢性荼毒的开始。
“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可以不把短剧代入现实,但是没有办法不代入三观。”她说。虽然如今很多短剧为了过审,会依据政策要求在结尾部分强行贴上所谓的“主流价值观”,但基本起不到什么正面作用。
那些“二次元与三次元切割”的说法很大程度是用来欺骗自己的,文娱作品的移情功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是显性的复制,而是钝性的内化,藏在价值观的缝隙里,慢慢发酵。
如今,宁惠已经主动降低了自己写稿的频率,每次项目结束,都会尽力让自己“从情绪系统中抽离出来”,努力恢复到那个能拥有对女性苦难的感知和质疑语境的自己。
*本文出现的受访者皆为化名。
*为避免文章配图出现虐女画面,采用空镜头的摄影作品呈现。摄影作品来自:Sharon。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作者:刘曳,编辑:Sh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