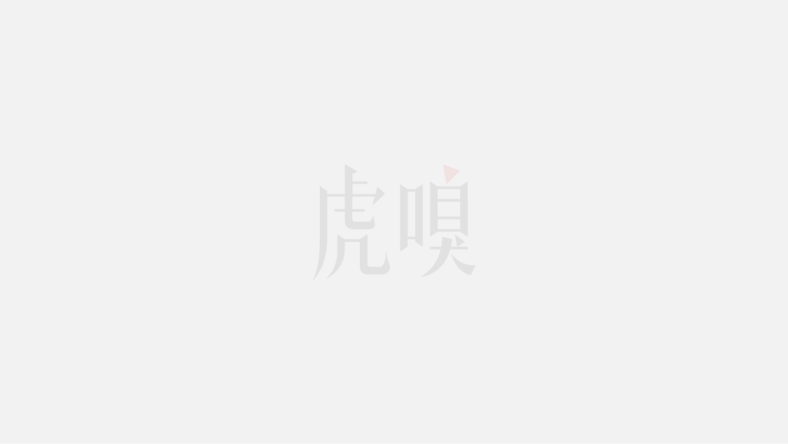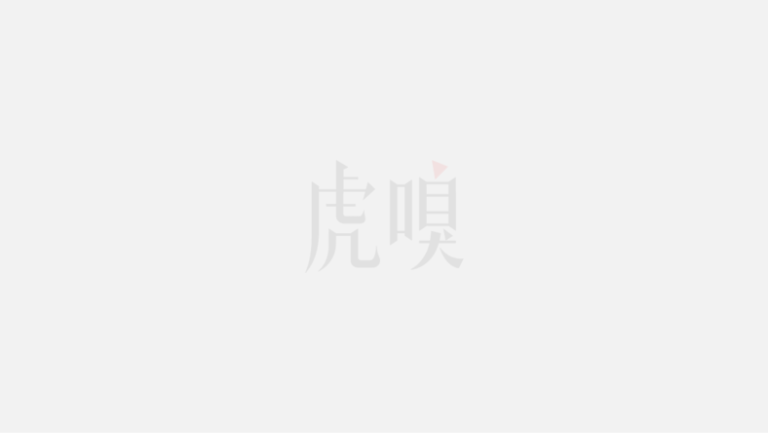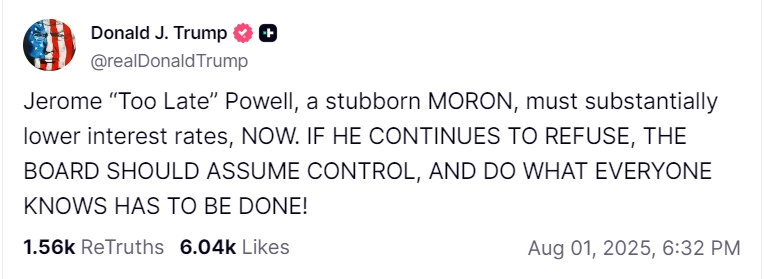【来源:虎嗅网】
从香港到温哥华,从首尔到纽约,作家查尔斯·蒙哥马利发现,一座城市的年轻感与幸福感,最关键的是自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刀锋时间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查尔斯·蒙哥马利
什么样的城市,看起来更有年轻感?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这座城市应该让人们更加亲近,更加快乐。现代都市的人口是高密度聚居的,一栋住宅楼可能住下几百人,人与人的物理距离非常近,但住户之间可能几乎不来往。放大到整个城市,不尽完善的道路设施、过于宽阔的街道、高大上的豪华商城、缺少绿色的CBD,都很难让人们的脚步慢下来,开始一场并不着急的交谈或漫步。
加拿大作家查尔斯·蒙哥马利(Charles Montgomery)长期关注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他创建了一个名为“幸福都市”(Happy City)的城市研究项目,尝试从中找到一个城市的快乐密码。
他有一个发现:如果整个城市是为孩子们设计的,那便是最理想的幸福之城。想象一下:
“我们沿着一条宽阔的大道走着,街上确实满是孩子,还有西装笔挺的商人,穿着短裙的年轻女士,小贩或是系着围裙、推着冰激凌三轮车,或是从小推车的烤炉里拿出玉米饼叫卖。……我松开车把,双臂举在空中,迎接凉爽的微风。我记起了童年时的乡村道路、放学后的散步、悠闲的骑行和那种纯粹的自由。”
他在《幸福的都市栖居:设计与邻人,让生活更快乐》一书中提到,要让城市变得更加年轻而有活力,对儿童及所有居民更友好,最有效的办法是为城市添加绿色。这是他在香港、温哥华、首尔、纽约等城市获得的经验。
以下是他在书中的分享。
城市居民也有一睹山脉的权利
加拿大温哥华花了30年时间让人们适应新密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已持续半个世纪的退居郊区潮。这场探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市民抗议把市中心包在高速公路“缎带”之间的规划,从而使温哥华成为北美唯一一座全无高速路贯穿核心区的大城市。
此后,温哥华也一直强硬地拒绝为汽车创造更多道路空间。最重要的是,周围的海洋、陡峭山脉及农耕保留地保护了这座城市,抑制了郊区发展,再加上稳定的移民流入,推动了市中心的建设热潮,并且在其他北美城市持续空心化的几十年里依旧保持了这一势头。
温哥华市中心是一个半岛,约有20个街区那么长,两面临海,覆盖着斯坦利公园的壮丽雨林。温哥华市中心经历了飞速的“脱胎换骨”。自20世纪80年代末,超过150栋高层住宅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而此前的六七十年代已经建造了百余栋。1991—2005年间,城市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在美国人争先恐后地奔向郊区边陲的时候,温哥华人则涌回市中心,熬夜排队等着房屋预售,甚至在公寓大厦还没浇筑地基的时候就抢着支付数百万加元。
这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悖论:温哥华越拥挤,反倒有更多的人想住进来,温哥华在世界最宜居地点调查中的排名也越靠前。在美世咨询、《福布斯》杂志和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各种生活质量榜单中,温哥华也是名列榜首或前几位。过去15年里,许多公寓套房价格翻了一番,即使经历了全球性经济危机,价格依旧坚挺。不仅如此,温哥华还是北美人均碳足迹最低的大城市,取得这一成就,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住得更近,因而降低了交通和采暖所需的能源。
温哥华的垂直城市探索既与众不同,也颇令人向往,部分原因在于它满足了居民对亲生命性的需要。新的市中心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本地人对景色的执着而展开的。尽管冬夜漫漫,温哥华人也几乎都不想去南方,因为那边经常下雨,太阳只会偶尔探头。他们本能地把目光转向了西北的山脉、雨林和海洋,换句话说,就是大自然粗犷的复杂性。
任何可能阻挡人们欣赏北岸山色的建设项目都会遭遇强烈的民愤。有鉴于此,城市规划者颁布了城市天际线的相关细则,在市中心创造出一条条“景观走廊”,让人们在山南的多个位置都可以便利地尽赏山景。实际上,规划者还迫使一些建筑公司改变了大厦的朝向,以保证人的视线不被遮挡。
住在高级公寓大厦里的人希望透过窗户即可欣赏自然风光的全景,而公众也有一睹山脉的权利,两者之间的张力促成了本地建筑标准的确立,也像曼哈顿那样,对建筑体积和采光的考虑塑造了一批又一批摩天大楼的形制。在楼宇越建越高的情况下,1916年纽约通过了区划决议,强制开发商缩减建筑体积,从而形成了曼哈顿标志性的阶梯状高楼,多少为街道保留了一点自然采光。
温哥华的垂直设计改造不是借鉴自纽约,而是来自香港。20世纪80年代,许多香港人来此定居。那时的香港土地稀缺,人口爆炸,建筑商们为容纳人口,采用了一种可以叫作“极限堆叠”的方法,常常是多层楼的商店和服务机构先组成庞大的裙房,在此之上再建五六栋甚至更多的高层住宅楼。进入此类复合建筑体,有时即便到了30层也可能完全看不到周围的山色。
这种模式在重视景色的温哥华必须调整。城市规划师把裙房高度减至三四层,也收窄了其上的高楼,并保证楼间距至少有80英尺,所以最终,天际线处仿佛是一群又高又薄的玻璃碎片,彼此间留有广大空间。于是,每位高楼住户都能欣赏到自然景色,街上的人也总能看到一点儿。在底部裙房,连排住宅或商业空间一字排开,因此街道依然安全且富有生气,琳琅满目的商店和服务机构让生活变得和在纽约一样方便。
这种设计模式大受欢迎,也让开发商有利可图,它因此催生了一个新名词:温哥华主义。圣地亚哥、达拉斯、迪拜等多座城市都有它的身影。但追随温哥华主义的各个城市似乎从未充分把握其精髓。也许是因为这些城市没有温哥华这般如画的自然风景,也许是因为没有几座城市能做到温哥华的程度,把高密度的好处极力返还公众。
“每天都要自然,这很关键”
人们对自然可能带来的好处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表明城市里的绿色空间不应被视作可选的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品。环境心理学家弗朗西丝·郭(Frances Ming Kuo)强调,人类若想健康栖居,自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天都要自然,这很关键。如果不能看见、不能触碰自然,你就无法享受自然的好处。邻近自然很重要,就算是零星的绿色都会颇有助益。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各个层面都将自然融入城市系统的建设,融入我们的生活。诚然,城市需要能让人与自然零距离接触的大型热点公园,但也需要家家户户附近皆有步力可及的中型公园和社区花园,以及迷你公园、绿化带、盆栽和绿植墙等等。吉尔·佩尼亚洛萨就曾指出,城市需要小中大号超大号等各种尺寸的绿色。否则,人类的生态系统就不完整。
如果城市和市民能改变关注的重心,那么即使在房地产高溢价的地方,亲生命性方针也能贯彻。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5年,当时韩国首尔的市长是敢作敢为的李明博,他下令把市中心的高架主路拆除了5英里,让其下历史悠久的清溪川重见了天日。挣脱了混凝土建筑的阴影后,现在的清溪川如一条玉带,流经草甸、苇荡、别致的角落和小小的沼泽,流域面积1000英亩。夏天开放的时候会有700万人来到这里,人们散步,躺在草地上,或在溪流的浅窝涤荡双足。
我曾在2015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到访清溪川。我离开熙熙攘攘的小商品市场一路向下来到河边,发现这里装饰着数百盏精美的灯笼,俨然一片夜色剧场。想要徜徉这片灯火谷地的人好多,市政府只得聘请一些年轻人拿着发光指挥棒疏导人群。
多年未见的各类鸟、鱼、昆虫也出现了。“以前你只能听到街上车流轰鸣,但现在你能听到潺潺水声!”一位已经退休的司机激动地说道。城市推出了新的快速公交服务,曾经填塞主路的车流消失了,城市焕发出了亲近自然的新生。
要提升亲生命性,运营不佳或未投入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是不错的着手之处,纽约高线公园(High Line)即是例证。这座线型公园位于曼哈顿西区,由废弃的高架铁路线改造而成,开始的几段,蜿蜒如荒野小径,长度超过19个街区,引导游客与他人,也与自然生态密切接触。
沿公园而行,游客不仅可以凌空一瞥附近的办公室和私人客厅,还可以走下观景台来到街上,而夜间的车流,在公园灯火的映照下宛若星河。而游客身边左近,则是数百种植物,有野樱莓、柳树、悬钩子、秋酸沼草,等等,其中大部分在铁路平台改造前就已经在这里生息。应邀来亲近自然,总会收获出其不意之感,其乐无穷。一个温暖的日子,我和一群陌生人一起,脱了鞋,在一处才没脚背的浅水塘里踩起水来。
自从高线公园开放以来,每座城市的规划专家就都疾呼建设自己的高线公园,但每座城市都独一无二,机会也是如此。比如洛杉矶市,就正在将市内32英里长的洛杉矶河——这条由混凝土衬砌的孤寂河道——改造为由公园和小径组成的“翡翠项链”。
城市可以留给自然的空间比我们想的要多。以伦敦的帕丁顿购物中心为例,这是一处高档的多用途区域,夹在帕丁顿火车站的铁轨和西路高架(Westway)之间。在我和我的团队向此片地产的业主英国地产公司(British Land)分享了自然对精神健康有益的证据后,他们很快将帕丁顿中心作为幸福改造的实验场。面积有限,所以他们把狭窄的王国街留给汽车的空间进一步缩减,以建设“林地步道”及香草园,并把水泥墙改造成垂直的生物丛林。这些变化对这里的商业大有裨益。研究表明,员工接近大自然,不仅会变得更加冷静、健康,效率也会更高。
和干预环境系统相比,在任何层面上,增加绿色皆能事半功倍。植物和水就是城市的空调(在首尔酷热的夏季,新生的清溪川沿岸比周边地区低3.6摄氏度)。植被能清除空气中的有毒微粒并制造氧气,捕捉碳并予以储存。城市也可以通过建设生态湿地(或半天然的路缘集水区)来管理地表径流,借此创造微观野生环境,在降低生态足迹的同时让城市放松紧张的神经。
现在我们知道,城市里的自然景观会令我们更加健康快乐。我们知道,自然让我们更加善良友爱。我们知道,自然能帮我们与他人、与自身生活环境建起重要纽带。我们若能在城市中添进自然的多样性、复杂性,特别是直接感受、触碰和体验大自然的机会,便可取得亲生命性挑战的胜利。达成这一点也不难:必须让生物密度成为建筑密度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