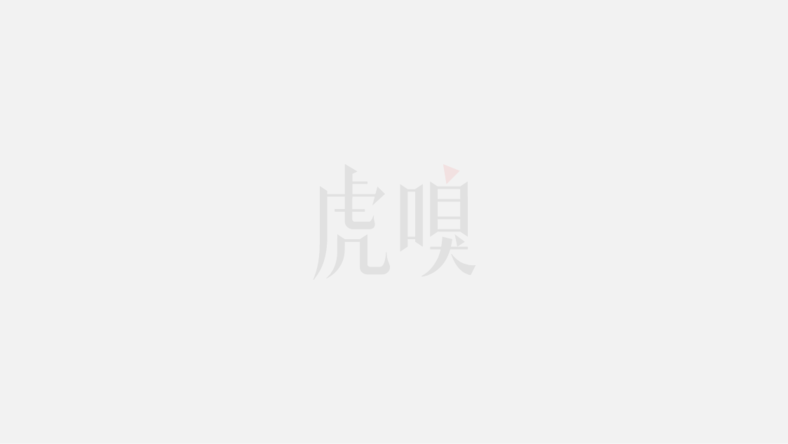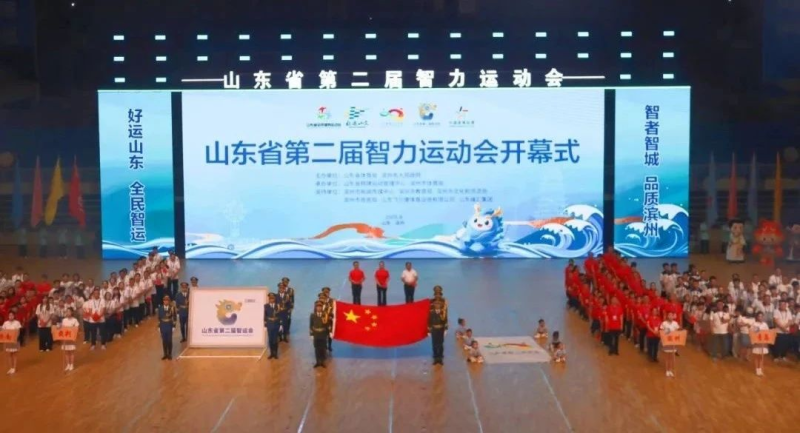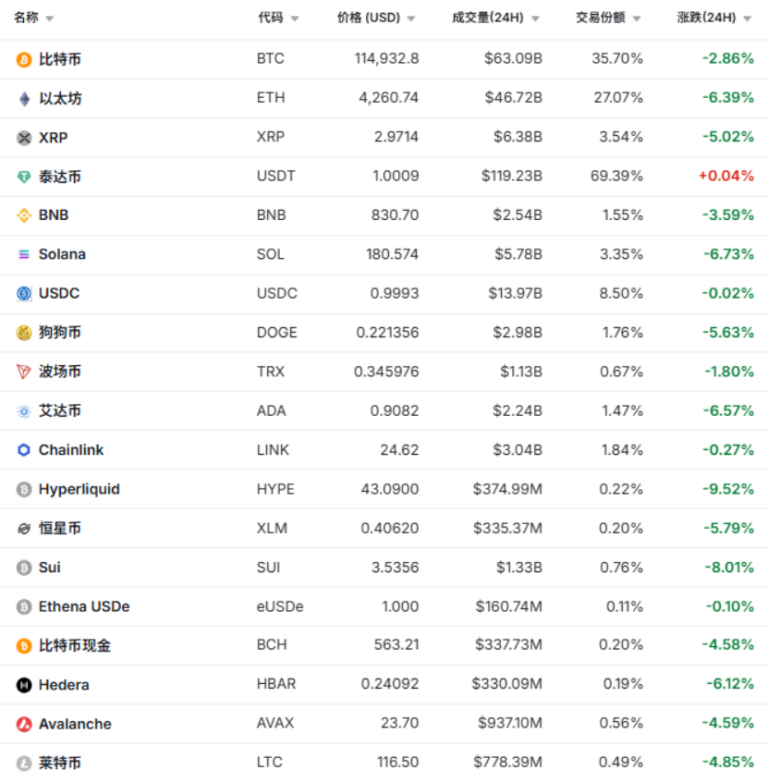【来源:虎嗅网】
我应该属于典型的小镇做题家,性格内敛,惯会考试。高考算超常发挥,进了省城一所211,专业是当下热议话题中打晕不报的新闻学。至大三,因课程任务参加了一场全国性比赛,拿了省奖,加分保研本校。
2018年,我顺利拿到文学硕士文凭。离编制最近的一次,是毕业前一年,在室友的鼓动下报名了当年的国考,买资料刷了几套卷子便束之高阁,但报名费已经交了,还是一起去参加了考试,笔试成绩出来,我和另一位考生并列第一。
那时候不明白工作的难以及体制的香,岗位选的是老家的国税局,当时不想回去,所以没有准备面试。
2017年,毕业论文答辩
2017年跑秋招的时候,最热门的行业还是房地产,万科中海碧桂园,一波一波的房企宣讲,场场座无虚席。我投了上十家房企,大多挂在无领导小组讨论,只有恒大进到了终面,最后仍然没有下文,现在想来,命运不让我走的路,或许也是在助我避坑。
最后入职的我司,是一家上世纪80年代就成立的国企,主营房地产开发业务,兜兜转转,还是没绕开地产。我完全不记得什么时候投的简历,公司名都没有念顺口,但苦于手上没有offer,我还是去参加了笔试和面试,公司大楼的一面墙完全被爬山虎覆盖,植物葳蕤,望去有一种与世不争的安逸。
面试和预想中差不多,一共只有7个竞争者,这家公司没有淘汰任何一个人。但最后签三方的时候,只有4个人来了,包括我。
与同窗们至少跳槽一两次的经历不同,我们在这家公司一待就是六年,也成了公司最后一届校招生。六年过去,我仍是部门最年轻的员工。
入职后,我被分到一个市区项目参与一线销售工作,在这个项目只待了2个月,又被派到一个郊区的合作项目学习历练。合作方是一家专门做豪宅的知名房企,前两年就已经爆雷,项目陷入舆情纷争,加上行业大势已去,以一年十几套的销量苟延残喘着。
在豪宅项目做策划,加班到凌晨2点插完小风车
派驻岗位是策划岗,开完盘后,原先的3个策划在一个月内相继离职,我不得不临时挑大梁,独自操办了一场中秋诗词晚会,这也是我作为新手策划的第一场活动,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策划和举办一场晚会。
活动公司的对接人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生,入行早,对这类活动轻车熟路,对接过程中也教了我很多,包括提前布场和演练,最后活动圆满完成。后来项目新招进来一个策划经理,刚好是我同校的学姐,后来又加入一个女孩子,加上我三个策划,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那时工作群里最高频的一个词,叫关闭时间,一个任务给出来,必定加一个关闭时间,经说今晚五点前,我传达到乙方那儿会更早,乙方传给自己的设计或文案,又会将时间提前,一环一环,这个行业,是快马加鞭的世界。
在远郊项目,也可以就地野餐
那时年轻,有无限精力,加班熬夜从不在话下,耳濡目染被灌输的思想,多是“别为失败找借口、多为成功想办法”。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的确是职业生涯中最接近市场化的一年,睁开眼就在想一天的工作安排,像是一台永动机。
我们三个策划都是女孩子,住在本地人都叫不上名字的郊外小镇,加班晚了一起去奓山CBD吃烧烤,这座沿318国道一字排开的远郊小镇总是被罩在灰蒙蒙的尘渣中,砖红色的大货车一辆接一辆从吃饭的摊位旁边驶过,尘土混着汽车尾气,为我们的街边大排档之旅添了不少江湖豪情。
入职第二年,我被调回市区的总部上班,开始朝八晚五的正常作息。公司五点半打下班铃。
调回公司第一天,打完铃办公室里的人立刻走光了,我在座位上惊诧不已,最后一个走的人在门口跟我说,“你要习惯准点下班的生活”。在此之前,我的确很少在天亮着的时候就回家,碰到节点活动,加班到转钟也是常有的事。
后来知道,我离开豪宅项目后,学姐和另一个女孩也相继离职,刚开始两人仍在地产行业内打转,学姐两年跳了三四个项目,又gap了一年,最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起了民宿创业。
另外一个女孩子,在一个高周转的项目里苦苦熬了一年多,把自己熬进了医院,果断辞职开始考编,最终如愿上岸。
我自己呢,回公司的第一年,先跟着部门前辈管理一个市区尾盘项目,主要是住宅交房、商业和车位的销售去化等一些收尾工作,比在豪宅项目的工作强度要低很多,基本没有什么十万火急必须加班加点当天完成的事情,整个生活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
生活变得松弛,可以慢悠悠吃早餐
有次和同事们一起出游,晚上在街头吃烧烤,大家说起进公司的时间,最短八年,多则十三年,一起细数往事,就是那种,你见过我的青涩我见证你的成长,大家待在一起,是细水长流的温情。
大家对后辈的关心和照顾,也像对待自家小辈。聚餐敬酒会按住我的杯子只让我喝半杯,因为住得远下半场让我不用去早点回家,走去地铁的路上碰到主管会一再嘱咐,丫头你早点回家啊。
也是在回到公司的两三年时间里,我得以不疾不徐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恋爱结婚生子,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部门同事也见证了我从初出校园到初为人母的样子。
和公司以外的地产人聊天,说起地产是人员流动特别大的行业,我拿自己公司的例子来反驳,对方会表示震惊,大概也会觉得,国企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地方。但我总觉得,围城内外,都是子非鱼的故事。
身在国企,除了本职工作,确实更能体会国企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自己身为其中一员所获得的认同感。我在2019年底回到公司,不多久疫情暴发,在家待了近3个月,那时感染风险仍然非常大,大部分在汉的领导同事都参与了防疫值守工作,脸上被勒出深痕,白大褂一穿一整天,没有退缩的人。
身在外地的人,每人负责一定数量的电话问询工作,我当时大约分到了60组电话,每日上午打电话问询这些居民的身体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其中有不少是孤寡老人,到后来还会和我聊天,谢谢我每天问候。
公司也有对口帮扶的贫困家庭,我加入公司团委以后开始跟进这项工作,每年不定期前往对口的村子看望一对由老人抚养的姐弟,特别是自己生育以后,对小朋友的境况更能感同身受。
国企也并非温室。2020年开始启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身在其中的我们,也成为最先感知到春江水冷的人。竞聘上岗、绩效考核、揭榜挂帅、内部优化,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变革接踵而至,有人通过竞聘升职,也有人被优化降薪,历史遗留问题在一一攻克,公司也开始拿新地。
在入职的最初三年,国企的确给了我厚植心底的勇气。我有勇气掏空家产买了房,不害怕因失业而断供;有勇气结婚,和一个差不多的人过一段差不多的人生;有勇气生孩子,休足产假和哺乳假,大体上能兼顾到幼崽。
刚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六年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不进国企我会不会是同样的人生进程,到底是国企选择了我,还是我活成了国企按部就班的样本。
后三年的新旧磨合中,经历了很多动荡与冲击。公司从富有年代感的老办公楼整体搬迁到整齐划一的现代化格子间,磨砂亚克力板挡住了左右同事,只听得见此起彼伏的键盘声和叹息声,像某种集体默剧的配乐。
那些钉在公告栏里的红头文件,像鸟类迁徙时掉落的羽毛,随便一阵风,就宣告一些人的职业生涯被吹向未知的方向。
远郊项目的两棵树
站在第六年的门槛回望,或许生活本就是不断校准重心的过程,既然无法预判下一阵风向,不如先停下来等靴子落地,过程中看顾好自己的健康,有余力时保持学习。
扎根未必需要永恒的沃土,能在时代夹缝里找到自己的湿度与光照,本身就是对无常最好的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