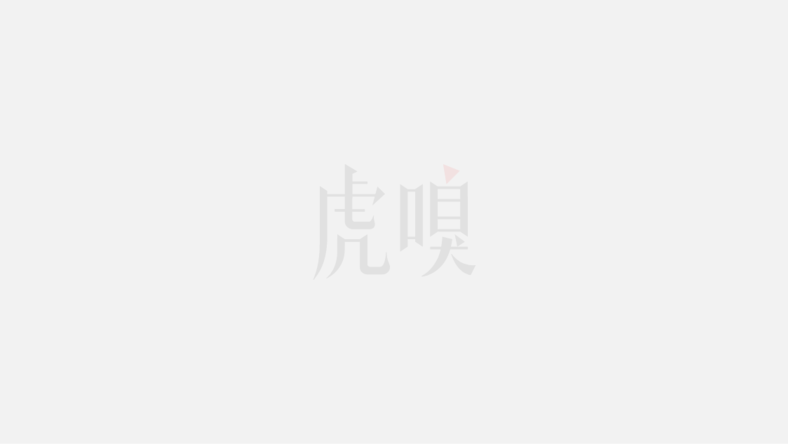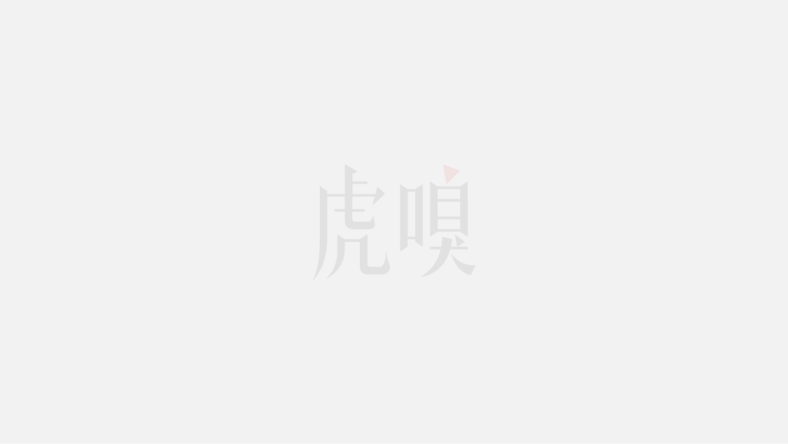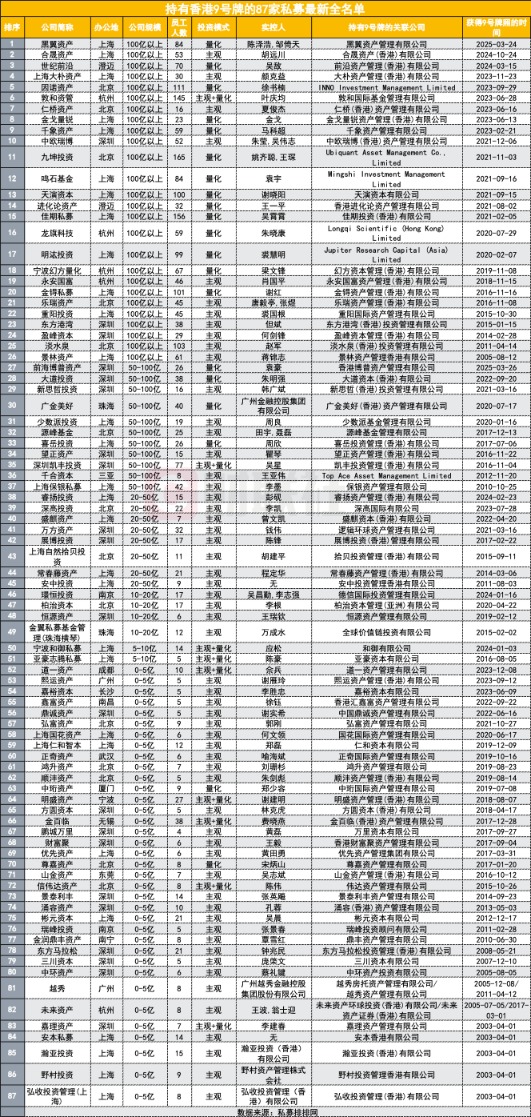【来源:虎嗅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刀锋时间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邹露,编辑:詹腾宇,原文标题:《写诗和做人一样,都要诚实|专访黄灿然》
很多读者了解黄灿然,是从他翻译的诗歌开始。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黄灿然翻译了苏珊·桑塔格、W.H.奥登、约瑟夫·布罗茨基和保罗·策兰等世界级文学大师的著作。他曾在中国香港《大公报》工作20余年,于2014年辞职后,移居至深圳洞背村,专职翻译和写作,是村里出名的“劳模”。后因租约到期,他从深圳的一座山搬到了另一座山,即大鹏半岛七娘山下。
毫无疑问,黄灿然是出色的诗歌翻译家,但别忽视了,他同时也是一流的诗歌评论家。在诗论著作《必要的角度》里,黄灿然以一种坚定、锐不可当的姿态,给出他对于诗歌和翻译工作的理解。
《必要的角度》
黄灿然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10
信、达、雅,他最看重“信”,也就是将原作者的声音清楚地传达出来。他在书中不留情面地批评思果为“汉语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董桥是“汉语卫生家”,并旗帜鲜明地捍卫直译的做法。
每一次阅读就是一次翻译。董乐山谈到翻译时说:“关键在于理解。”黄灿然在书里指出,这句话道出了翻译的要害,它适用于任何体裁的翻译。他认为,“诗歌也有真相要讲,那就是语言的真相。”
《必要的角度》首次出版于1999年,是他青年时期的作品。但这本书所透露的他对于诗歌、翻译和语言的思考,放在今天仍然观点独到,且毫不过时。去年,此书终于再版,广受好评。
《必要的角度(增订版)》
黄灿然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明室Lucida,2024-8
诗人的责任是什么?黄灿然很认同约瑟夫·布罗茨基这句简单的判断:“写好诗。”但问题在于,何为好诗?黄灿然显然不是什么诗都捡起来译,他坦承自己只翻译那些最一流的诗。一首诗的好坏,决定了译本的好坏。
我问黄灿然,如何判断一首诗是好诗?他以“诚实”二字作答:“好东西的一个基础是诚实。做人要诚实,其实是很难的。做诗要诚实,也许更难。”他也一直是以“诚实”要求自己的。
“在普通的好诗和不同寻常的诗之间,我选择后者”
《新周刊》:你说,每个诗人都有好诗、一般的诗和坏诗,应当挑选好的诗来译;原诗是否好、是否可译,决定了译诗的好坏。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却也考验了译者的判断力。在纪录片《日常的奇迹》里,你只考虑译最好的那些诗,这也意味着你不太会照顾读者。首先我想问,对你来说,什么样的诗是好诗?会不会有一个判断依据?其次,为什么你只翻译最好的诗歌?这会意味着对读者的罔顾吗?
黄灿然:这里包含几个问题,如果要详尽回答,每个问题都得用一篇长文来阐述,而且还未见得令人满意。还是从简单的例子说起。
首先是避俗,俗套的俗。不说诗歌,就说我案头某本书的前言:“中国近代是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古老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完了……新兴的资本主义步履维艰地……文学是一面镜子,它从不同方面……”于是你知道,作者是在一个俗套的框架里运作他的思维,写些连他自己读起来也没有感觉的文字。甲眼中的好诗,在乙眼中可能是坏诗,反之亦然。所以说好诗没有标准。
具体判断一首诗的好坏并不容易,但判断一位诗人的好坏却相对容易,因为有作者的全部作品作为参照系。如果是翻译某位外国诗人(的诗作),则又有文学史及同行的评价作参照。例如,我介绍卡瓦菲斯的时候,就引用了多位外国堪称伟大的诗人对他的评价,目的就是提供参照。因为卡瓦菲斯的诗看似很写实、很简单,似乎也很容易。
提供参照,是为了引起中国读者尤其是诗人们的足够重视。我其实也是在暗示,诗人和普通读者有可能把卡瓦菲斯的诗当作很一般的诗,在致力于避俗的诗人眼中,卡瓦菲斯有可能也是俗套的。
回到刚才那段俗套的引文,如果另一位作者走到另一个极端,用诡异而委曲的方式表达,是不是就是好的呢?他避俗了,但也不一定就是好的。因为避俗只是一个基础,说不定还得避雅。说不定还得避两者之间的折衷。
瞧,我似乎触及建立衡量标准的困难,因为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是,我这样描述的时候,你是否隐隐感到,“避”本身也是一个陷阱?似乎好东西是有意识地“避”某种倾向或有意识地“求”某种倾向。但好东西往往是不避也不求。可是俗套的东西也往往是那些不避也不求的人写的!于是我们再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就是好东西的一个基础是诚实。做人要诚实,其实是很难的,做诗要诚实,也许更难。
两天前我刚看到一篇关于李鸿章的文章。李鸿章晚年跟身边的人聊天,言必称“我老师文忠公”曾国藩,似乎他的成就都是曾国藩教导的结果。他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他打算从事洋务的时候,去拜见了曾国藩。
曾国藩问他跟洋人打交道有什么策略,他说他打算“打痞子腔”(耍滑头)。曾国藩给他的建议是一个“诚”字,并说:“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李鸿章回忆说:“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
曾国藩话里的“虚强造作”,差不多就是我说的那种又避又求的倾向,好的作家都知道诚实“不至于过于吃亏”。不过,这是从作者的角度来看的,跟我们判断好诗似乎又没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又说了一番废话了?但是只要作者是诚实的,他自有一种精神,一种氛围,就卡瓦菲斯而言,就有一种语调,散发出来,变成某种吸引人的气质和魅力。
还得再具体一些。就拿我最近出版的《奥登诗精选》来说。恰好,奥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作家。我挑选他的诗的时候,回避他一些俗诗,例如《葬礼蓝调》,这只是歌词而已;还有不少人物诗,例如写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倒不是写得不好,只是还不够独特;我尽可能挑选从他自己的生命体验里流出来的。还有一些很好的歌谣,我也暂时避开了,之所以好还要避开,是因为他还有一些写得并不完美,但却有非同寻常的表达方式的诗。在普通的好与不寻常的表达方式之间,我选择后者。
《奥登诗精选》
[英]W.H.奥登著,黄灿然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2024-8
此外还有各种考虑。一本诗集这样选下来,难度高的东西就比较多,也就是说,这本《奥登诗精选》的读者对象,是诗人,而不是普通诗歌爱好者。这样,是会失掉一些读者的。对出版社和我自己的版税收益来说,也是有损失的。
读者的品位是要慢慢培养的,像卡瓦菲斯,最初的读者对象也是诗人,经过第二、第三版,读者慢慢从诗歌界而至文学界而至文化界扩散。
信、达、雅,信是第一位
《新周刊》:你向来提倡用直译的办法来翻译现代诗歌,但你也说,现代诗歌常常晦涩难懂,有很多“吃不透”的部分。当年你向巫宁坤请教翻译托马斯的过程,他说自己“没有把握”,你说这正是巫宁坤翻译托马斯的重要性。对于很多水平一般的译者而言,他们会首先“解决掉”这些“没有把握”的部分,而不是将它们移植过来——你认为这是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养分。可以讲讲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吗?在你自己做翻译的过程中,遇到“没有把握”的时候,你通常是如何应对的?
黄灿然:我好像在《必要的角度》里也提到过,赵元任在翻译上很开明,但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虽然如此,有些词还是不宜直译,例如dramatic,如果翻译成“戏剧性”,恐怕中文读者无法理解。但当他这篇文章在20多年后被译成中文时,“戏剧性”早已家喻户晓。显然,对赵元任来说,“戏剧性”不只是“没有把握”,而且是“很有把握行不通”的。
至于一般的没有把握,也不是真的那么没有把握。假如我对“辩证法”一无所知,但这不妨碍我把“辩证法”翻译到中文里。假如我对原文里“落日的铜板”没有把握,由于“落日”和“铜板”都是名词,而且我为了谨慎把原文词典里的“落日”“铜板”条目的各种解释都查了一遍,我还是可以颇有把握地把我没有把握的“落日的铜板”移植到中文里来的。假如我遇到一个新词“篮球场症候群”,由于我已经知道有各种症候群,所以无论我对“篮球场症候群”有没有把握,我都可以把它直译过来。
真正的没有把握是确定某种词在某个结构中的确切意义。假如我在原文里遇到“落日的铃铛”,虽然也都是名词,但“铃铛”既是一件器具,也是一种声音,可能还有别的意味。这时候我就得“排查”:除了查原文词典里“铃铛”条目的各种解释,还得查其他研究著作,看看专家们有没有提出特别的看法;以及查作者著作中有没有相关的指涉。
最极端的是完全看不懂,通过各种办法,可能历时数月甚至两三年也没搞明白。例如桑塔格《论摄影》里有个很短的句子,我读不通,从开始翻译到最后一校,好像有两三年,隔一段时间就查。最后才想到把不通的句子改成符合语法的句子,然后再查。果然,好几个作者在引用这句话时,直接就把它改正了,或注明“原文如此”。就是说,桑塔格的句子是不符合语法的。当然,这种极端例子,最常见的是作者在书中引用别人的话,录入引文时发生错讹。
《新周刊》:直译不是死译或者硬译,你提出了一个有力武器是“非个性化”,要还原诗人的风格,而不是自以为传神地发挥异想。在《译诗中的非个性化与个性化》那篇文章里,你列举并对比了四位中译者对洛威尔《黄鼠狼(鼹鼠)的时刻》的译本,把何为精确的词语和句序表达明确下来。你认为译者接近“非个性化”的要义是什么?我想起你在《日常的奇迹》里说,翻译很像是一种服务业,服务于读者,一个不好的服务,通常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吗?
黄灿然:“个性化”有点像我前面提到的过于“避俗”和“求雅”,因而有点像曾国藩说的“虚强造作”。而“非个性化”大概相当于“诚”。诚信诚信,也是信、达、雅的信。
《新周刊》:你会在意读者对你的译本的反馈吗?比如有些读者评论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幽暗且晦涩,将看不懂归结为翻译的问题。“读者认为看不懂是因为翻译差”这样的意见,对你而言是重要的吗?
黄灿然:我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理解翻译》里列举了各种读者的层次。翻译跟创作一样,你只是译给、写给你理想中的读者看。但总会有不是你理想中的读者慕名而来,失望而去。这部分读者假以时日,也有可能会转负为正的。
我忘了两个都是翻译还是一个是翻译、一个是创作的例子。在我的豆瓣小站上,有读者相隔几年,其中一个刚好相隔十年,在同一篇译文或创作下第二次留言,说自己当年无知。我不会对读者的劣评做出反馈,但如果有读者通过留言或来信指出具体某个错误,我会感谢并记在我的标有“校对本”的书里,以待将来修改。
想起一个例子,刚好是保罗·策兰的。一个读者来信,指出我译文中一个词译错了。他的信好像很不客气,或不礼貌,我忘了,但我只对我译错(看错字)的那个词做出反应。我感谢他,表示将来再版会改正。过了可能有一年多吧,那位读者又来信,对自己上次信中的不礼貌(大概如此)表示歉意。这些例子都表示读者在鉴赏和修养上不断提高自己,而且我相信他们将来对待其他作者、译者,肯定会更谨慎,不会贸然下判断。
《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
[德]保罗·策兰著,黄灿然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雅众文化,2021-1
到底什么叫“纯洁的汉语”?
《新周刊》:你在《“恶化”与“欧化”》一文中提到:“很多指责当前中文或译文水平差的人士,往往误把这种‘恶化’归咎于‘欧化’,这对欧化是不公平的。这种混淆,并不利于建设纯洁的汉语,甚至可以说是有害的,因为它阻止了欧化的健康发展,而欧化的健康发展与汉语的健康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对于“纯洁的汉语”这个说法,我多多少少有些排斥。在后篇《汉译与汉语的现实》中,你驳斥了思果和董桥的翻译要翻成“像中文的中文”的做法,显然,你并不认同让汉语复归传统的保守做法。
黄灿然:“纯洁的汉语”应该是顺着维护汉语的思路说的吧。如果汉语是水,我想谁都希望汉语是纯洁的。但偏偏有人自己并不喝死水里的水,却认为它更好,并名之曰净水,而有些人——应该说,大部分人——则凭本能直觉就选择活水、净水。
那些提倡汉化汉语的人,是十分奇怪的。譬如说思果,他的汉语水平,在我看来充其量也就是中下吧;他大概一段文言文也写不出来,更不要说古文了(因为如果按他的思路,则文言文还不够,最好是古文,而古文最好是周秦古文,汉以下都还不够古);另外,他连一个长句也写不好(我在书中有举例的)。
《翻译研究》
思果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8-3
我们再看钱锺书,他主要写文言文,也能写很好的白话文(《七缀集》),他在文言文里译外国人的片言只语,都是用文言文,但当他正儿八经译一篇长文,他就欧化了,很长的句子,很多的“的”字——就应该这样嘛。
另外,复杂的长句并不是西文里才有,也不是翻译里才有,我记得《史记》里就有很复杂的长句。但拿个更近、更现成的例子,桐城派的方宗诚有一篇《古文简要序》,第一段主要由三个长句构成,第一个很复杂,有159个字;第二个有107个字,第三个则有70至90个字左右——视乎你如何标点。
这篇文章网上随便能找到,动辄以汉语之美、短句之美批评欧化句子的读者和批评家,不妨先把方宗诚的长句拿来揣摸揣摸,再计算一下自己花多少时间读通弄懂,然后再计算一下自己花在读他们认为欧化的长句时,又花了多少时间读通弄懂。
《七缀集》
钱锺书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
《新周刊》:我很好奇,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如果存在一个方向的话,你现在认为应当是怎样的呢?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你提到过,汉语的活力可以由两种方式达成:一个是向古典文学取经;二从翻译作品吸取养分,通过陌生化语言达成新的思维模式。能否理解成你期待的、健康发展的现代汉语,实质上是使用中文的人的思维是健康的?
黄灿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某种被某个人或某些人认为“应该”怎样的语言。但某个人或某些人可以在写作中实践自己“应该”怎样的语言。
在某些重大的转折发生时,例如废除文言文,采用白话文,进而发展现代汉语这样的重大转折,或采用简体字这样的重大转折时,不管个人或某些人觉得应不应该,都已经是既成事实。但个人仍可以在写作实践中反抗或修正这些重大转折带来的影响或后果,例如,他可以写文言文(例如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或不那么白话或不那么现代汉语的有文言文倾向的语言;又或者,如果不喜欢简体字的话,就从事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只出版繁体字竖排的书,或只在使用繁体字的地区出版著作和发表文章。
《谈艺录》
钱锺书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0
我的一些论述与其说是“提出”或“提倡”某些看法,不如说是反对某些人提出或提倡的看法,或他们在实践中所体现的受某些人的提倡所影响,或已经不是某些人提倡的影响而是某群人或某个时期固化的并且显然已经无效的语言观念。
对写作者而言,面对不公平才是常态
《新周刊》:在《作家与政治》中,你提到,存在两种作家:一类是为艺术良心而作,另一类是为社会良心而作,二者是相通的,因为前者以突出艺术良心来彰显社会良心,后者亦如是。看到这里我在想,一个没有良心的诗人,在什么社会情境中会获得不公平的嘉奖?
黄灿然:很难说别人没有良心,更不能说自己有良心。不妨从更普通的层面上说。差的或不够好的作家获得不公平的嘉奖,这种情况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我想它的价值是锻炼好的、但得不到公平的嘉奖的作家的耐性和韧性。因为,怎么有可能只要你写出好作品就得到公平的嘉奖呢?
你20岁写了一首好诗,就应该得到公平的嘉奖吗?难道不是你到50岁写了100首好诗才得到公平的嘉奖,甚至仍然得不到公平的嘉奖?因为你越早得到公平的嘉奖,对于那些比你不知好多少倍的作家——例如杜甫和陶渊明——来说,就更不公平了,因为他们都是死后又过了不知多少辈子才得到公平的评价,甚至嘉奖也没有,而你竟然狂妄到要在这辈子中得到公平的嘉奖?一个写作者应有的“公平”的态度应该是:不公平是常态,公平是例外,嘉奖是意外。
黄灿然与导演许鞍华。在许鞍华拍摄的纪录片《诗》中,黄灿然是重点采访对象。(图/《诗》)
《新周刊》:你觉得诗歌存在一个终极目的吗?在《相信诗歌》中,你介绍了希尼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你写道:“诗歌是清白的,一如平民,真正的诗人没有理由使自己或使诗歌沦为斗争的工具。”若诗人要对社会有所介入,应当以怎样的方式?
黄灿然:诗歌不应该被诗人或别人或任何意识形态使用或利用。相反,应该是诗人被诗歌使用和利用。至于诗歌怎么利用,或诗歌有什么意图,那不是诗人能揣测的。确实有诗人介入社会这种说法或诉求。只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人们会把诗人介入社会看得好像比诗人下海或诗人炒股更高些。
《新周刊》:你曾说,“诗歌的真相乃语言的真相”。你是否也思考过语言的真相是什么——如果存在的话?
黄灿然:在英文里,“真相”与“真理”是同一个词。很难想象谁宣称自己掌握或知道语言的真理。
2024年度刀锋图书奖全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