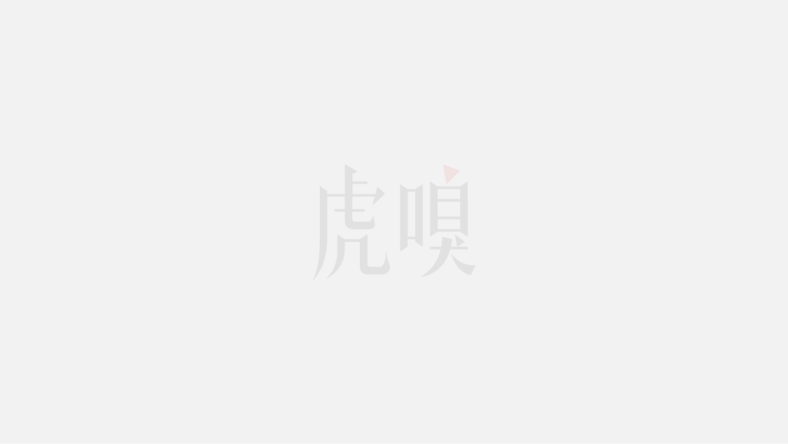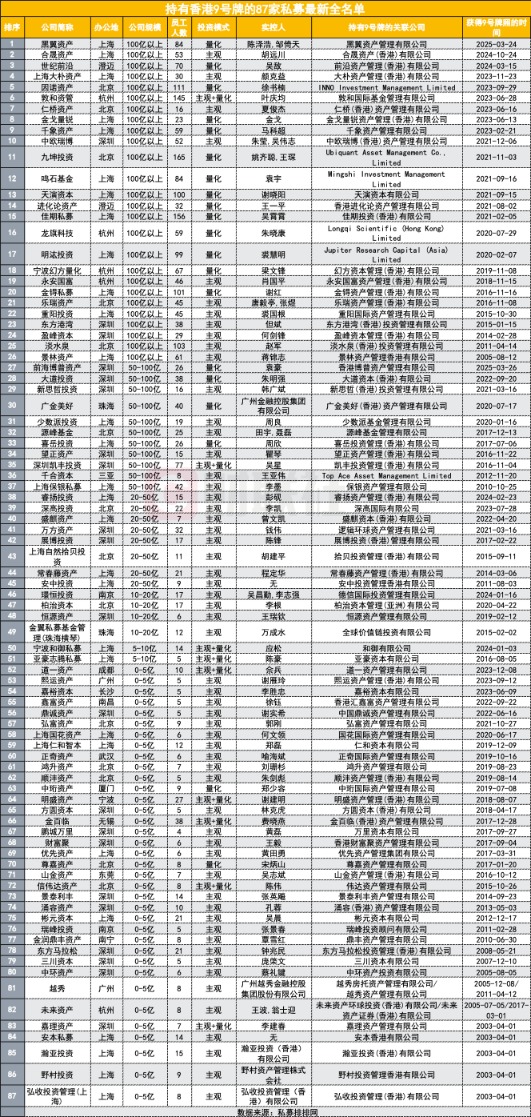【来源:虎嗅网】
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纽约大学教授乔纳森·海特在2024年出了本新书,贡献了他对美国年轻一代观察思考。
你只要扫一眼封面,你就能知道这本书想要谈什么,主标题是大大的“焦虑的一代”五个字,副标题是“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
《焦虑的一代》探讨了自2010年代初以来,青少年(尤其是出生于1995-2012年的“Z世代”)焦虑、抑郁、自杀等心理健康问题大幅上升的现象。
乔纳森认为,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童年的数字化重构”,即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改变了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和心理发展路径。
乔纳森说对了一些事情,但把00后、10后这样数字原住民的焦虑寻根溯源为数字化生活方式,不免有失偏颇。
没有手机真的会更开心?
先来看看乔纳森的分析路径。过去二十多年,儿童养育环境和方式的巨变,过去的童年以户外玩耍、面对面社交为主,现在则被孤独的屏幕时间和线上社交取代,乔纳森将其概括为从“玩耍童年”转向“屏幕童年”,这点很传神。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乔纳森注意到Jean Twenge等学者分析了美国青少年2010年后的心理健康数据,发现青少年抑郁、焦虑、自杀念头和自杀率在2010年后显著上升。研究进一步发现,每天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越多,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越高。尤其是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超过3小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大幅增加。
据此,乔纳森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高涨,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高度相关。
为了支撑这一发现,乔纳森援引了多份外部的研究,最典型的有以下两个案例:
Instagram母公司META内部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女孩表示,使用Instagram让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形象感觉更糟。学术实验也发现,青少年在Instagram等平台上频繁进行外貌比较,容易导致自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另一个权威案例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项实验,让青少年在类似Instagram的环境下浏览图片。当他们的照片获得更多“点赞”时,大脑的奖赏中枢(如伏隔核)会显著激活,与获得金钱奖励时的反应类似。与此同时,看到别人获得更多点赞时,青少年也更容易模仿和改变自己的行为。
乔纳森据此得出结论,社交媒体通过“点赞”等机制,强化了对外界认可的依赖,削弱了自我调节能力,增加了焦虑和社交压力。
缺钱、少爱、学业重才是大焦虑
乔纳森这本新书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童年的数字化重构”这一新概念,他展示了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普及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恶化的相关性,但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
Z世代其实是信息技术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
2018年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青少年的调查显示,81%的青少年认为社交媒体让他们更容易与朋友保持联系,69%的人表示社交媒体让他们能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许多青少年表示,社交媒体帮助他们在遇到困难时获得朋友的支持,增强了归属感和情感联结。此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7年发布的《数字世界中的儿童》报告指出,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为青少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表达和创造力空间。他们可以通过视频、图片、文字等多种方式展示自我、表达观点、参与社会议题。
今天,离开了互联网、智能手机、数字技术,基础教育几乎难以开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报告指出,数字技术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信息获取渠道,有助于提升信息检索、批判性思维和数字素养。
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学会2017年发布的《Status Of Mind》报告指出,社交媒体为青少年提供了心理健康信息和互助平台,许多青少年通过网络社区获得了情感支持、心理疏导和专业帮助。大家应该多少在YouTube和Twitter、国内的b站等平台上刷到过相关大量的心理健康科普内容。
Z世代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上升,更可能与经济压力、教育竞争、家庭结构变化、社会不平等等多重因素有关。国际顶尖学术期刊Nature Reviews Psychology
和生活在一百年前的人一样,经济因素仍是导致人们心理健康的最主要因素。
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RCPsych)2021年报告称,这一年,生活在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发生率是高收入家庭的2到3倍。歧视、社会排斥、资源获取不平等等社会结构性不平等,是心理健康危机的重要背景。
美国心理学会(APA)2020年发布的《压力在美国》报告称,在2020年的调研发现,67%的Z世代受访者表示经济压力是他们主要的压力源,而千禧一代为60%,X世代为53%。该报告指出,Z世代对经济前景、就业机会、学业负担等问题的担忧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群体,疫情、经济衰退、就业市场不稳定等因素加剧了Z世代的焦虑和抑郁。
对于求学阶段的年轻人来说,学业乃是焦虑的真正源头。
世界卫生组织(WHO)2021年针对45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健康行为调查(HBSC),发现学业压力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预测因子之一,约40%的15岁青少年表示“经常或总是感到学业压力”,与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睡眠障碍)高度相关。研究指出,教育体制的高竞争性、升学压力、成绩排名等因素,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情绪健康。
亲子沟通不畅、家庭支持缺失也是心理健康风险的重要因素。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2023年青少年风险行为调查(YRBS)发现,来自非传统家庭结构的青少年报告抑郁、焦虑、自杀念头的比例显著高于双亲家庭。
一代人有一代的焦虑
00后、10后的父辈、祖辈们比他们更焦虑。
就拿50后来说,他们是典型的“生存一代”,他们童年时期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生存压力远比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了,温饱和安全是他们小时候的首要问题。青年时期,他们中大部分会赶上文革,教育中断,甚至还可能要离开家里上山下乡,度过一段磨练的知青岁月。回城之后,又经历工人、干部的分流,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多次转变。
70后更像是“夹心一代”,童年时期普遍赶上改革开放,物质条件逐步改善,青年时期面临高考压力、就业分配向市场化转型,大部分70后都会经历同样的社会巨变,包括国企改革、下岗潮、住房市场化等社会剧变,身份和经济压力大,在传统与现代价值观之间摇摆,既要追求稳定又渴望突破。
相比前后的几代,80后既没有50后、60后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也没有90后、00后那种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和多元选择,他们作为最后接受纸质媒介教育,但最早遭遇互联网冲击的“数字移民”。
在过去四十多年里,80后几乎经历了整个国家从绿皮车到高铁,从筒子楼到大平层,从积贫积弱到世界工厂的巨变,80后为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付出了多重代价,他们在社会转型的夹缝中成长,既是现代化的受益者,也是压力和牺牲的承担者。
《中国心理健康蓝皮书(2022)》显示,80后的焦虑指数(23.6%)仍高于00后(19.8%)。2021年《新周刊》“中国焦虑地图”调查显示,80后是“最焦虑的年龄段”,焦虑来源包括房贷、子女教育、职场压力、养老等。于是更为通透的90后、00后选择了不婚不育,斩断焦虑的来源。
所以说,每一代人都在各自的历史节点上,承受着各自的社会之重。就像在电视剧《奋斗》中,80后男主角陆涛在天台大喊的那句话:“我们必须先找到那面墙,然后才能知道门在哪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波波夫同学,作者:波波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