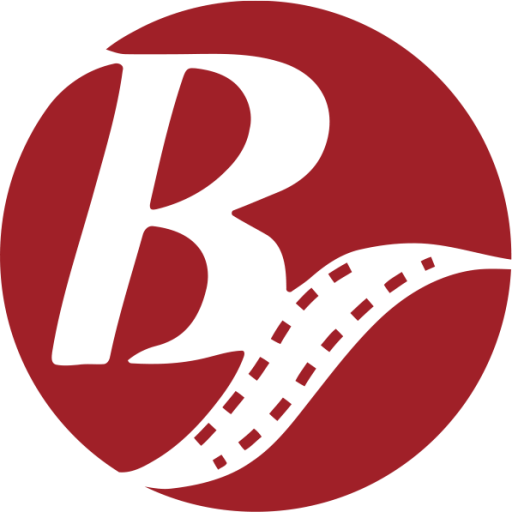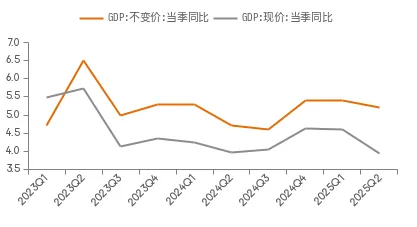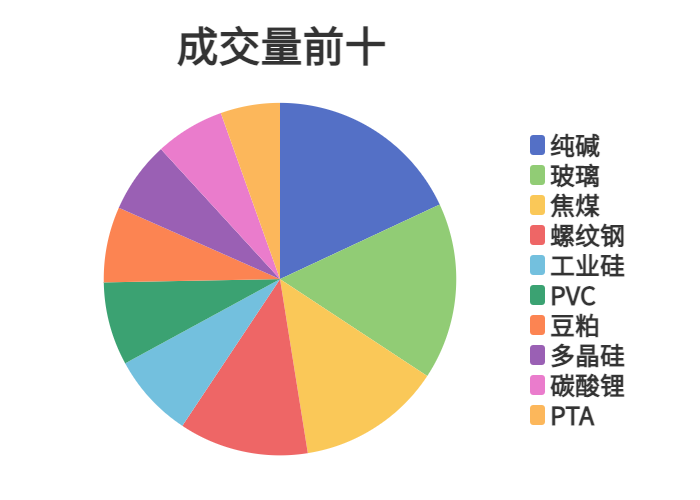【来源:虎嗅网】
一
这是我们为数不多,全程用上海话对话的选题。是出于有意识的控制,否则很容易就跑普通话那边去了。
仔细想想,也挺有意思,虽然我们一直在写上海,但平时开会、讨论的语言是普通话。
走访的时候,即使对象是上海人,整场对话中讲普通话的含量也会高于上海话。只有在街采时,碰到上海爷叔阿姨,才大概率会全程使用上海话。
在广东路股市沙龙街采时,我们用上海话
这样的个案多少能描摹出上海话的现状,它的使用场景和频率正在减少,甚至有的人会担心,它会不会慢慢消亡?
语言的变化和这座城市的变化一样快,30多年前,情况几乎完全相反,当时很多人对上海很不习惯的一点是,上海人怎么如此广泛地使用上海话。
在90年代的报纸上,有不少关于外地人到上海因为语言不通导致的不便。
1990年8月《文汇报》的《吴语听不懂,难煞异乡客》一文中,一名山东读者对编辑吐槽:“十几天下来我非常纳闷,上海人不讲普通话,在推广普通话已30多年的今天,不能不让人遗憾。”
1997年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内容就是:莫让“阿拉”成了“拦路虎”,拜托大家都来说普通话。
1990年代公交车上都用上海话,陆杰/摄
我们做上海话系列选题,并不是拜托大家都来说上海话。就像沪语研究专家钱乃荣曾在采访中指出,“目前是有两派在争论,一派要保护上海话,一派则希望顺其自然。我主张顺其自然。很多时候,正是因为语言使用得不顺其自然,才会走向衰落。”
我们是想通过走访和观察,展现上海话在这个时代的使用流变。
语言是一门工具,有需求就会用。有的上海人开始不说上海话,也有非上海人开始学习上海话。我们这次文中的两位主人公,学会上海话,有个人的需求,也有时代和环境的推动。
二
第一次见到竹阿姨,是在朋友家聚餐,当时她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
我后来问朋友:“你找了个上海阿姨啊?”
她说不是,阿姨是浙江嵊州人,来上海很多年了。
哪一年来上海的,竹阿姨一下子说不上来。她只记得是儿子7岁那年的7月1日。“我儿子1991年养的,那应该是1998年来上海呃。我第一次掼脱小人,一个人到上海来,残古啊,所以日脚总归记牢的。”
竹阿姨刚来上海的时候,很多上海人家还在用马桶
大姑子比她早几年到上海,给她介绍了在鲁班路照顾一个风瘫老太的工作。“格辰光工资低,350元一个月。”
但即便如此,对当时的上海家庭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为那一年,上海人的平均月工资为1005元。
和全程需要服侍、端屎端尿的工作量相比,老太的子女或许在担心这个工资留不住阿姨,所以同住的儿子儿媳在楼里询问,谁家要倒马桶。一番询问之下,竹阿姨又接到给两户人家倒马桶的生活,一个月多挣50元。
“格辰光,都是有老虎窗的老房子,大家还都在用马桶。”
从那个时候开始,竹阿姨就在慢慢转换她的语言。
“我没文化的,普通话讲不好。刚开始只能讲阿拉乡下土话。但是老太一家都讲上海话,我一点点跟着讲,就会讲一点上海话了,不过还是学不像的,有乡下口音。”
在老太家做了5个月后,竹阿姨开始去做钟点工,她做工的区域集中在襄阳路嘉善路一带。
“我没脚踏车,都是靠两只脚奔的。”她最忙的时候一天可以做14个小时,那时钟点工的行情是3元5到4元一小时,竹阿姨接了七八家人家。
竹阿姨的工作区域在襄阳南路一带
雇主家有点共性,全是上海人,大多是老人,只请一到两个小时。“打扫卫生就一个小时,加做饭才变两个小时。”
即使在老太家熏陶了5个月,但竹阿姨的上海话还是不好,“有的时候东家会问,侬讲啥?不会有人教你,得靠自己,刚开始去的时候就尽量少讲话,只说几句必须要用的话:‘阿姨爷叔,今朝做啥?哦,我晓得了。’他们讲的时候我就认真听,慢慢的再搭一句搭一句搭出来。”
“我跟这家人家讲几句,跟那家讲几句。每家都学两句,就学出来了。”
和竹阿姨一样,她的大姑子的东家也都是上海人,所以她也会说上海话。
20多年过去了,请钟点工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过去那样需要“雪中送炭”的上海老人家庭,而是多了很多需要分担家务琐事的年轻家庭,他们很多不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新上海人,所以后来的阿姨不一定需要会讲上海话才能在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
“像和我一样在上海待了很多年数的浙江阿姨,大多会说上海话,安徽、湖南、湖北的阿姨大多讲普通话。”
竹阿姨过去的雇主都住在弄堂老房子里
竹阿姨大多都是老东家,有些从老人七八十岁做到了去世,“有一个从80岁不到开始照顾,到90多岁走脱,还有个老先生是103岁走脱的。”
不过有一些人家因为搬家而不做了,“有的搬到浦东去了,有的到宝山去了,他们市区里房子不要待。”
竹阿姨觉得她会说上海话这一点让她在找新东家的时候大有利处,“人家一听就知道我在上海待很久了。会讲上海言话,他们欢喜点。”
新找的东家虽然也是上海家庭,但不是之前的语言环境。“小孩是讲普通话的,家里来照顾的外公外婆说上海话,妈妈爸爸会说上海话,但互相之间说普通话。”
现在她不用像之前那样奔波了,每个家庭房子面积都大了,最起码都要两个小时了。
在上海那么多年,现在竹阿姨工作生活都用上海话,“不过乡下口音还是要吐出来呃。”她笑着说,“说上海话的辰光有乡下口音,但现在回乡下,上海口音也要吐出来呃。”
三
“明丽美发”开在外滩后街的元芳弄。老板周明丽讲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几乎听不出口音,但她其实是扬州人。
明丽美发位于外滩后的元芳弄
1992年,19岁的周明丽到上海学生意,在杨浦区工人新村的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师父也是扬州人。“扬州不是三把刀嘛,理发刀也是阿拉那边特色,像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读书机会不多,出来的人蛮多的,大家就侬带我来,我带侬来(上海)。”
在来上海之前,周明丽能听得懂一点点上海话。“因为江浙沪有点相通的地方,听起来不是很吃力。”
在杨浦的理发店里,师父和周明丽说扬州话,和客人讲上海话。
“阿拉接触的都是上海人,做头发的上海阿姨妈妈们都讲(上海话),好像多讲多讲,就会讲了。”
“30年前头,阿拉客人三四十岁,正好是要做头发的辰光,(从那时)跟阿拉跟到现在,这帮人比较欢喜讲上海话。”
明丽接触的客人都是上海人
很难用方法论概括出周明丽学会上海话的路径。但彼时的上海,上海话是主流。
“1992年来的时候,公交车上都是上海人。国营店蛮多的,国营的都是上海职工呀,连理发店最早也是国营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海人还维持着出门说上海话的习惯。
在这样的环境中,周明丽自然而然、不知不觉之间,就能说上海话了。
周明丽在帮客户烫头,彼此,人们交流都用上海话
这个过程,是从听懂、开口说一些简单的句子,到慢慢会用上海话拉家常。
“一来就大约摸听,听听听听就会讲了呀。一直听伊拉讲,‘侬汏头啊’‘侬剪头发啊’,就格能讲起来了。”
“吃饭、汏衣裳,格种最基本的(上海话),像单词一样的学起来。”
“单词会了,再模仿。模仿声音、腔调,一句句会讲的。”
“最主要我觉得,不要怕难为情,就格能瞎讲八讲,讲讲就会了。就跟学英文一样的,侬讲法讲法,就会讲了呀。”
“阿拉格种服务行业,接触的人本身就是上海人,侬讲得不对,人家也不会笑你。讲错脱不要紧的,最多笑笑,笑过就好了呀,下趟就晓得了。”
除了客人都是上海人,理发师的工作也会和顾客产生生活交流,这进一步造就了周明丽学习上海话的日常环境。
“一边剪头发,一边茄山河,像茶馆一样的,聊工作、聊家庭、聊小孩,聊社会上的事体。阿拉格种环境,不是一本正经、不好讲言话的,实际上就是(上海话)讲得比较多。”
在客观环境之外,周明丽虽然没有刻意学习上海话,但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她的潜意识里也有意愿学习。在当时,在上海学说上海话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
“比较要好的客人,人家像长辈一样的,会讲‘倷小姑娘来上海学生意哦,一定要学会上海话,交流起来比较方便,包括谈朋友啊。侬会讲上海言话,人家和你交流上就没障碍了’。”
1997年,周明丽结婚了,丈夫也是上海人。于是,除了工作,在家庭氛围中,周明丽也使用上海话交流。
这样一个渐渐学会上海话的过程,也是妹妹周秋香在上海的生活路径。
周明丽的妹妹周秋香
周秋香是80后,1998年到上海浦东歇浦路的一家理发店当学徒,那时她16岁。
在姐妹俩的回忆中,俩人听懂上海话大约都花了2到3个月时间,而可以用上海话日常交流,是在到达上海2年后。
周秋香学习上海话的过程,也是自然而然地。在野生的沪语环境中,周秋香一点点学会了更多上海话表达,一点点纠偏。
“格辰光老板娘烧菜给我们吃,伊钞票给我,叫我买白乌龟(上海话:鹅),我想wū jù、wū jù,个末我就去买了莴苣,上海人讲香莴笋啦。我买了很多香莴笋,被伊穷讲,出了个笑话。”
但是周明丽的弟弟,2002年大学毕业后到上海生活至今,还不会说上海话。
“首先伊年龄比阿拉(来的时候)大了,工作环境都讲普通话。伊也廿年蹲下来了,到现在上海言话不会讲的。”
“阿拉阿弟学过的,但是也没学会。伊还拿本书学,从‘买菜、汏菜’(根据生活场景一点点学过)。伊听得懂,但是一句句讲出来,就不是很流畅。”
“我觉得学语言最主要是环境。”
“对,有时候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周秋香补充道。
也许学会一门方言,除了环境、意愿,也需要一点点天赋。
曾经,周明丽的店里来过一个河北学徒工东东。东东在店里待了8年,非常有意愿学习上海话,但临到他离开上海还是没有学会。
“东东廿二岁。阿拉专门惹伊,问伊几岁了,伊讲‘两岁’‘纳尼岁’,哈好白相。”
“和地域也有一点关系,北方人好像是学不大好,伊老认真地学,但讲来讲去,学不好。”
明丽美发已经开了二十多年
时间一晃,周明丽从杨浦的学徒工,到1994年到机电局理发室工作,到2000年开了属于自己的理发店,她在上海已经33年了,超过了她在扬州待的时间。她说普通话的时候,甚至有了沪普的味道。
“蹲扬州廿年,蹲上海已经三十二年了,生活习惯、讲话思路,我觉着(已经上海化了)。回去阿拉同学聚会,讲扬州言话,伊拉讲我口音有点点变化。”
我们曾经写过《上海人“沪普”考古》,讲沪普的人其实是在用上海话进行思考。
等到周明丽和周秋香的下一代,年轻人是在用普通话思考。
周明丽的女儿是95后,小时候在家里说上海话。后来去美国留学,等女儿回上海的时候,周明丽觉得她的上海话有点“怪”。
“伊小辰光会讲的,后头去美国待了大概五六年,回来交关上海言话也不标准。我听阿拉女儿上海言话表达得蛮怪的,语音语调、用词也怪。”
“掼浪头(上海话:说大话,显示自己有能耐),伊也不晓得的。”
“格人立升很大的,伊讲啥么叫‘立升’啊?(立升:资产雄厚)”
周秋香的儿子是05后,上海话也没有母亲说得好。
“阿拉儿子从小也是说上海话的,后来自从去了幼儿园,好唻,又返回普通话。”
“我问伊今朝上到第几课了,‘十两课’,伊上海话已经有点忘记了,实际上应该‘十二课’。”
“阿拉格辰光有氛围,现在没啥氛围了。现在上海小囡,都不会讲上海言话了。”
对于新世代的上海小囡来说,他们的上海话或许停留在孩童时期。面对没有见过的事物、逐渐消失的事物,作为孩童没有习得的词汇,他们已经不会说了。
周秋香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
“阿拉客人衣服不是都吊在后间嘛,我讲侬自家拿只丫叉头,叉下来哦。客人阿姐讲,要西唻,阿拉孙女都不晓得丫叉头是啥物事,侬辣么生(突然)来句‘丫叉头’。”
“个末(生活中)不需要这个物事了呀。”
参考资料:
1. 罗涌才,《拜托——请大家都来说普通话》,解放日报1997.09.22;
2. 徐蓓 邓天飞,《上海话里的城市文化密码》,解放日报2013.11.1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上海市民生活指南,作者:顾筝、姜天涯,编辑:小泥巴,摄影:姚祖鸿,绘图:顾汀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