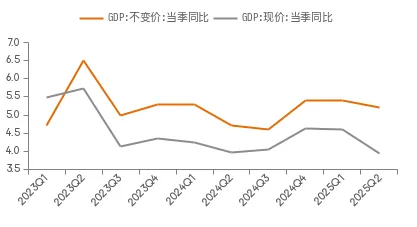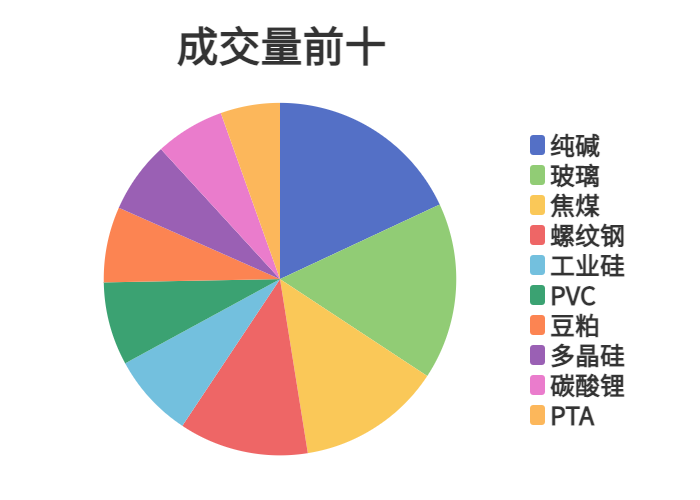【来源:虎嗅网】
2024年的冬天,王芳芳望着独自坐在阳台上的母亲,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老去”的重量。半年前父亲离世后,母亲的生活骤然失衡——曾经结伴散步、一起玩游戏的日常,化作日复一日的沉默与电视机的嘈杂。
社区的托老所成为了王芳芳为母亲在居家养老中寻找到的喘息站。托老所,类似托儿所的老年托管机构,王芳芳母亲白天去和其他老人聊天、做手工,有专业的照护人员看管;晚上回到家里吃晚饭,她和丈夫照顾老人休息。这看似轻盈的解决方案背后,是中国养老困境的复杂切面: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我国80岁及以上老人为3580万人,他们的子女大多迈入“50+”门槛,在赡养父母与抚养孙辈的夹缝中挣扎;传统养老院因费用高昂、心理抵触遭冷遇,居家养老又困于精力与专业照护的匮乏。
托老所的出现,试图填补这道裂缝,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日间服务,让老人保留“家”的归属感,同时缓解子女压力。
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当下,托老所正成为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的“中间解”。这里能为老人提供哪些生理与心理支持?托老所的存在能如何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什么样的“老年友好社区”才是我们所期待的暮年安放之处?
失衡的居家养老生活
王芳芳产生为母亲寻找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的想法是在2024年冬天。
半年前父亲去世,母亲虽仍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大部分工作日的白天都是独自一人待在家中。父亲去世前,两位老人每天在家做伴,下午时会一起出门散步,会用电脑的父亲还会带着母亲玩一些诸如连连看、俄罗斯方块的游戏。
父亲的离世打破了这种平衡,腿脚做过手术的母亲很少再一个人出门,唯一的娱乐方式变成了看电视,反反复复看的都是《神探狄仁杰》《重案六组》等年轻时已经看过许多遍的老剧。王芳芳每天出门上班前会替母亲把电视打开,有一天她出门有些急,忘记了帮母亲开电视,回家时发现她坐在阳台的小板凳上,痴痴地看着窗外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
在几乎“社交死亡”的生活里,王芳芳发现母亲的性格也逐渐发生变化,过去体面、高学历的母亲在她回家以后变得尤其多话,常常拉着她讲自己今天在电视中看到的内容,“就像刚刚去读书的小孩子一样”。但随着母亲独自一人在家的时间越来越长,王芳芳发现母亲的语言能力有着逐步退化的趋势,有一次想要复述一段电视剧情节,却磕磕巴巴了半天没有说清楚,“而且我知道这部电视剧她看过好几次,当时就觉得她可能有一点阿尔兹海默症的倾向了”。
不仅如此,有时母亲还会认错人,用王芳芳姐姐的名字叫她。芳芳的女儿和女婿每周都会回家吃饭,有次回来时,母亲拉着外孙女婿叫一个家里人都没听过的名字,大家听到时心中都浮了一层担忧。
看着尚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母亲,王芳芳觉得送她去养老院过于残忍,加之母亲一听到养老院高昂的费用便连连拒绝,王芳芳便打消了送她去养老院的想法。但她心中清楚,为母亲寻找一定的社交活动已经刻不容缓,此时家附近的社区提供的老年日间照料服务进入了她的视野。
每天早上九点前将母亲送去社区的养老日托所,这里有专业的护理员和陪伴老人的老师,白天会带着老人一起聊聊天、做做手工,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老人自己回家或是由家人接回家一起吃晚饭。王芳芳发现在餐桌上,母亲变得比以前开朗了许多,愿意主动和大家分享在日托所干了些什么,还会骄傲地拿出自己白天做的手工和家人分享。看到母亲的改变,王芳芳的心中终于松了一口气。
孤独与裂痕:夹缝中的养老困境
王芳芳与母亲的故事在国内并不少见,恰恰折射出中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普遍的生存困境: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都很难完全贴合他们的需求。
在和日间服务中心生活的老人聊天、沟通的过程中,王芳芳发现许多老年人有着严重的“养老院羞耻”,对于机构养老的抗拒心理十分严重。
之前一位长期在服务中心日托的老人性格倔强,不仅不同意孩子送他去养老院,甚至连日常走路都不愿意使用拐杖,某天在家里不小心摔跤骨折了,才最终去了养老院生活。
“他们会觉得去了养老院,就是承认自己不行了。”小白在沟通中发现,许多老年人都会认为去了养老院“就是等死”,只有到了完全走不动路或是无法自理的程度,才会点头同意。中国社科院2022年的调查显示,73.6%的老年人认为“与子女同住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仅12%的受访者接受机构养老。
对于大多数社会参与程度较低、社交关系简单的老人来说,家庭是他们的情感核心,入住养老院常被视为“被家庭抛弃”的标志,触发强烈的失落感和自我价值否定。而在传统孝道文化中,“居家养老”被默认为子女尽责的表现,而机构养老在老一辈人心中则有着“家庭关系破裂”的意味。
经济因素则是另一个养老院不被老人们接受的原因,在上海,养老院每月每位老人的费用在4000~10000元不等,高端养老院的月费用则会高达20000元以上,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许多老人年轻时省吃俭用,一听到这笔高昂的养老支出便连连摇头,不愿意给子女增加沉重的负担。
但居家养老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如一座大山,让身处其中的子女只能在夹缝中艰难呼吸。小白提到,大多数80岁以上的老人,子女年龄也在50岁以上,已经是“小老人”的年龄。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仍需要每天上班、工作,白天没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老人;有的需要帮子女照顾小孩,时间精力都无法全部分给老人;哪怕没有这些束缚,“他们也需要自己的社交生活”,无法全天陪伴老人。
“小老人”困境本质是快速老龄化与家庭结构小型化碰撞的结果,他们不仅需要承担养老责任,还需要为子女提供育儿、经济等支持,大多数人都会有一种身心俱疲的感觉。在未来,独生子女家庭中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凸显。
徐晴的父亲今年年初突发轻微脑梗,因为送去医院及时,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但行动和思维的灵敏度都大不如前。尽管父亲已经年近九十,但过去身体一向不错,在家里能自己做饭,闲暇时还喜欢在阳台上侍弄花草,徐晴和丈夫外出上班时并不需要太操心。
轻微脑梗后,父亲很难自己解决午餐问题,每天都需要徐晴或是丈夫提前一晚或是早上早起半小时为他准备菜饭。偶尔几天还好,时间长了,徐晴和丈夫难免会因此发生争执,尤其是两人工作都忙的时候,“就会出现推卸责任的情况”。有时父亲嫌弃准备的饭菜不好吃或是不丰富,更加剧了家庭矛盾。
无法否认的是,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机构养老,当老年人在家庭中从支配者成为了被支配者,他们都需要跨越不小的心理障碍。养老院的环境相对封闭,每日的作息非常规律,大部分老人甚至无法决定自己每天何时吃饭。这种统一化管理会让老年人感到失去生活掌控权,加剧对衰老无力的恐惧。
居家养老同样会面临类似的困境。小白所在的服务中心里有一位95岁的老太太,独自一人生活在过去的老房子里,女儿在郊区买了一栋别墅后,试图将她接去一起生活。两星期之后,老太太从郊区别墅里“逃回”了老房子。
在和老太太聊天的过程中,小白了解到,她不愿意接受家庭中地位倒置的现状,“过去都是她管女儿,现在是女儿管她,比如安排她吃饭、洗澡,她接受不了这种情况”。白天,女儿和女婿出门上班,小孩出去上学,老太太一个人在家没人可以讲话,让她更怀念起了日托时认识的老姐妹,索性便自己搬回了老房子住。对于高龄老人来说,角色倒置与家庭地位变化很可能引发抑郁倾向,尤其在丧偶老人中,自我价值感丧失的风险会进一步增加。
居家养老难以为继,机构养老又遭抵触,正在普及中的养老日托服务成为了城镇家庭养老的一个喘息站。
养老日托:从“看管”到“重建生活”
小白在上海杨浦区长海路街道的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工作,这里从1999年开始就为附近的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2019年,社区想要进一步规范“养老日托服务”,便和小白所在的养老服务机构合作,开设了现在的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老人每天早上九点来到服务中心,下午三点到四点回家。
长海路街道属于老龄化十分严重的社区,周边常住的居民里有超过50%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但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里却只有12位长期接受服务的老人。
在小白的观察中,高龄、丧偶的老人是最愿意来到日间服务中心生活的。长海路街道的服务中心里一共有12名长期进行日托的老人,年龄基本都在85到95岁之间,年龄最大的一位今年已经98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60~80岁年龄段的老人可以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满足自己的社交需求,“他们在六七十岁还能走能跳,可以到外面和人玩,不一定需要到我们这边来”。
在这里,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倒热水这样有安全隐患的事也会尽量交给专业的护理员来做。
每周给老人洗澡前,小白都会和大家强调:身体有不适不可以洗,但是有的老人不想浪费一周一次的机会,仍然会强忍着不舒服进浴室。洗澡过程中,每15~20分钟就有工作人员去浴室门口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小白记得有一位老人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依旧进去洗澡,工作人员在询问时发现她昏迷在了浴室了,紧急和家属联系后,工作人员打120将老人送去了医院。尽管老人没有受伤,子女也没有无理追究,但小白想起这件事仍然觉得心有余悸。
“有的老人很固执,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么慢慢跟他沟通,要么选择去和他的子女谈。”不过在六年的工作过程中,小白发现很多老人的生活习惯并不能因为中心的规定就该改变,“我们这里有个阿姨,非要把毛巾随便乱放,你跟她说过了,她也不改,你也不能和她犟,最后还是随她去吧。日常中如果不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大部分时候都随便了。”
小白每周都会为12位老人安排活动:周一画画,周二听健康讲座,周三做手工,周四看电影,周五打麻将。遇到一些特殊节日,他们也会开展相应的活动,清明节一起做青团,六一儿童节开办小型运动会(其中的项目都是夹弹珠、纸杯传球这样锻炼手脑协调度的游戏),七一建军节唱红歌、看红剧等等。
“之前政府主管的时候主要是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待着的地方,有个人在看着就行;我们更多是考虑到老年人的行动力、心理健康状态,来安排各种活动,这完全是两种考虑方式。”
在多年的相处过程中,小白逐渐摸清了每位老人的性格。有位阿姨喜欢唱歌,便会在开展活动时让她来领唱;另一位阿姨擅长手工,每次做手工时就会安排不那么擅长的老人和她一起;运动会时,外向的老人往往都会有一个内向的搭子。
在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工作的六年里,小白发现越来越多的老人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她记得不久前一位老人过九十岁生日,特地拜托自己的女儿买一些糕点礼盒送给中心的老师、护理员和老人。
“这件事情她会反复地讲,她女儿也会打电话来问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老人的数量。老人会觉得自己的生日是一个喜事,需要和大家分享,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我们需要怎样的“老年友好社区”?
在政府补贴的支持下,长海路街道的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每月的收费仅为250元,在基础的每日照护服务外还提供每周一次的洗澡、每月一次理发和扦脚的福利。在小白的观察中,哪怕是250元,老人对于这笔费用仍然十分敏感,许多人会在心中计算这250元可以吃多少顿饭。
“很多子女会给老人算帐,你每个月交250元,可以理一次发、扦一次脚,每周可以洗一次澡,夏天冬天房间里都有空调,家里电费都省了,大家还能开开心心地一起玩,很多老年人就会觉得很划算。”
250元一月的费用对于周边老人来说是十分友好的服务价格,但对于社区来说,仅仅依靠老人所交的费用,连一位工作人员一个月的工资都发不了。尽管政府有一定的补贴支持,但相对于专业的养老院来说,专业的照护资源非常短缺,12位老人仅有一位护理员。
因此,在招募老人时设下了相对严格的条件:老人需要神智清晰且有自理能力。大量残疾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无法被接收。再加上日间服务中心并不提供接送服务,许多住在五楼、六楼的老人哪怕有电梯也不方便走到社区来,更不用说很多上海的老小区并没有配套电梯,加大了老人去日托中心的难度。“这些相对特殊的老人,他们也有很多需求,但是我们无论是硬件方面、软件方面还是经济支持方面,都很难去接收他们,比如我们缺少有专业康复理疗资质的护理师。”
在养老日托中心以外,一个“老年友好社区”需要更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以分担居家养老的压力。小白所在的长海路街道还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了家庭照顾床位和长护险服务。申请长护险的老人在评估认证后,会有持证上岗的护理员到家里照顾老人,帮他洗澡、照顾起居,每小时的价格为6.5元。家庭照顾床位则需要家庭自主购买服务包,由拥有资质的护士团队,每月的价格在5000~7000元上下,与长护险结合能够覆盖不同经济水平、健康状况的老人。
尽管政府已经在大力建设“15分钟养老圈”,但落到实处,仍有巨大的资源与需求错配问题。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23年研究显示,上海长护险护理员日均服务8户,单户服务时间不足40分钟,仅仅只能维持老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很难进一步帮助老人重建生活。家庭照顾床位则需要智能床垫、紧急呼叫器等自购设备,对于经济条件普通的家庭来说,可行性并不高。
相比较而言,无论是社区配套设施还是专业资源服务,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在养老日托服务中的尝试都值得我们借鉴。东京、大阪的养老日托中心则开始利用AI、机器人、VR康复等科技,帮助行动不便、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人提高生活质量。
东京、大阪、京都的养老日托中心还会鼓励老人制作一些手工艺品在市场上销售,销售收益用于公益。东京一家养老日托中心与托儿所共享场地,每日安排共同活动,如手工、唱歌和园艺,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也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日常活动中。
养老日托为中国养老提供了一种“中间解”,但它远非终点。当老龄化以加速度逼近,如何让日托服务覆盖更广人群,如何弥合专业资源与政策支持的断层,仍是悬在“老年友好社会”目标前的巨大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