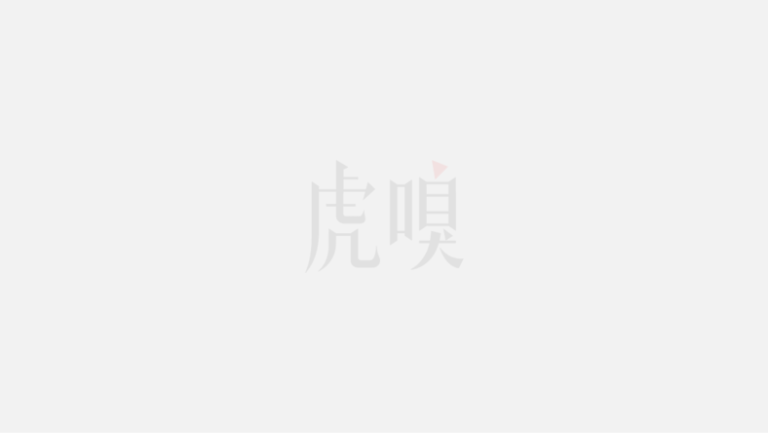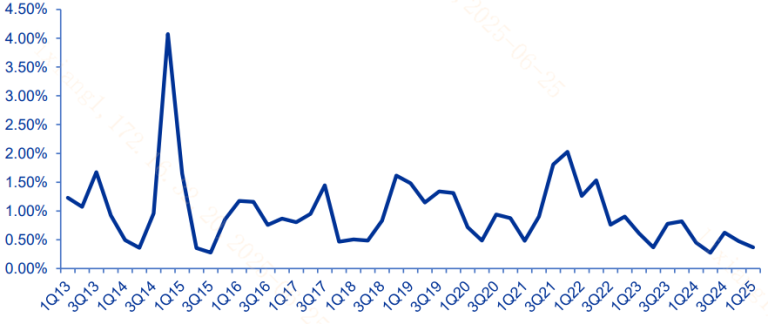【来源:虎嗅网】
今年2月,日籍华语作家吉井忍的新书《格外的活法》出版,她用七年的时间,走访了12位“不那么主流的普通人”。这十二人的选择颇为有趣,他们中间有二手书店店主、兼职垃圾清运公司职员的搞笑艺人、给黑道做文身的人……这些人既没有进入典型的资本主义劳动体系,又不是那种典型意义上离经叛道的人。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走向了自己眼前的营生和信念,“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但仍然非常认真地面对普通的生活”。
在此之前,大家对吉井忍的认知可能来自于她此前所著的另一本书《东京八平米》。吉井忍曾经在东京租了一间只有八平米的房间,不能洗澡、不能做饭,但省下来的钱可以花在精神生活上。“居所”的边界被模糊,整个东京都被当作自己的客厅——她将“自己的生活哲学”在八平米中细细展开。
我在通勤的时候连着看完了《东京八平米》和《格外的活法》,合上书只想感叹:真好啊。如果不是为了采访,这或许就是我唯一的评语,随后带着一种无形的慰藉继续生活。
然而,一旦站到媒体人的位置上准备采访,我开始不自觉地替这本书搭建结构、归纳关键词、提出主张,试图为这本书找到“公共意义”。
在和吉井忍通话之前,我以为我们会有很多共识。但真的聊起来,对话却有不少卡顿与错位。我的语言被轻轻推回,而她像一个坐得稳稳的石头,守住一种实在。
事情就是这样,不多、不少,不需要赋予不属于它的光。吉井忍没有给出明确或定制的答案,也不为他人代言。《格外的活法》并非意图呼吁读者突破常规的人生,而她笔下的那些人不是榜样,不是反叛者,不是社会批判的样本,只是一些活着、还在试着活得更好的普通人。
同温层太闷,我宁愿被冲撞
BIE:在《东京八平米》中,您住在一个八平米的房间,面积只够起居和上厕所,于是,您将家当作卧室,把东京当成家的“客厅”。而在《格外的活法》中,您则走入12位生活在社会主流视野之外的他人的生活。
您在《东京八平米》里展现的活法,和《格外的活法》里受访者的活法,有没有相互映照的关系?
吉井忍:从时间上说,我在过着《东京八平米》那样生活的时候,就去采访《格外的活法》当中的人。但《东京八平米》是自己非常私人的经历和生活,而《格外的活法》是以采访者或者说撰稿人的身份去联系和采访其他人,所以我的心态和文字当中是几乎没有自己的。我只有一个任务:我要把对方的状态尽可能地写出来。因此,对我来说它们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两本书。
但是我之所以选择这十二位受访者,可能就跟我的经历、我的人生观有关系了,所以两本书不能说完全没有关联。我过着东京八平米那样的生活,所以我可能关注到那些人,或者说我需要偶遇像那样子的活法的人。
BIE:是的,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您在这两本书里边盛放的生活哲学是连贯的,提醒着我要和世界沟通,而不是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边,过一种没有别人的生活。
吉井忍:是的,现在我们不出门、不跟别人接触也能轻松获得信息,活下去是完全可以的。但因为跟其他东西没有具体的关系,我们很容易进入一个非常漂浮的状态,这样的话也很容易焦虑。
这次我在北方做了一些宣传活动,几乎每一场活动里读者问答环节,都会有人举手说:“我们现在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这怎么办?或者说,你有没有类似的焦虑?”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每场活动都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后来想一想这个事还是理所当然的、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也和后面的经济状况有点关系吧。
BIE: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常常因为自己的生活没有参照而感到焦虑。
吉井忍:也许我写《格外的活法》也是寻找自身参照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我没有选择那些在大媒体上频繁出现、声音很大的受访者?我不会去找他们,可能我觉得,反而跟那些人之间没有太强的关联感。状态跟我相似的人,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好像是站在这个社会边缘但还能活出自己的人。那些人才是我想靠近、想学习,或者能作为参照的人。
所以,我选择采访对象时,没有明确的标准,我写的时候是靠直觉:这个人挺有意思,我想去采访。但是后来想一想,可能是因为当时我的状态就是需要那些人,我就是想跟他们聊天。
BIE:有点像照镜子?
吉井忍:照镜子只能看自己吧。如果以这样的心态来接触别人的话,好像是同病相怜那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像。我不希望这样子。
甚至可以说,我需要对方来侵犯、破坏或者否定我所谓“好”的一个边界。
BIE:现在很多人认为要向内去挖掘自己的内心,做一些冥想、自我疗愈、寻找内心平静的事情。我好像前几年也会这么觉得:人的内心很丰富,可以关起门来自己找答案。您书里呈现的好像是完全不同的姿态,不是要逃到内心里边去,而是要走出去撞击世界,和人产生关系,在关系里边看清自己是谁。
吉井忍:是的。我想,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和这个世界建立关系呢?
如果“去哪都一样”,何不原地动起来
BIE:这些受访者的生活状态也让我很有感触。主流奋斗叙事逐渐失效的背景下,曾经有一种“田园牧歌”的叙事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很流行。大概是上班族辞掉工作,离开城市,去旅行、去种地。
但是您选择的这些采访对象,并不是要切掉和城市以及社会的联系,倒像是要在社会里,找到那么一个不太寻常的、但自己能够全然投入的“生态位”。这是一种特意的选择吗?这和您自身的经历有没有关系呢?
吉井忍:并没有特意的选择,但是肯定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系。更年轻的时候我会去一些很远的地方。我在成都留学的时候,大概一半的时间都不在成都,拼命去各地旅行,包括新疆的阿勒泰,也有一段时间在东南亚旅行,去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那些地方走过一遍。
那时候我有种寻找新的自我的感觉,但是我最后的结论是:我到哪儿都是我自己,逃不掉的,这是一种近乎惨烈的感觉。90年代的时候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坐72个小时的大巴才能到阿勒泰。那是个太远的地方,但是我到那里却发现自己真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你真的是去哪都一样。
后来在法国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特意选择在农场干活,因为我还是有点憧憬就在农场比较悠闲的、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生活状态。我非常享受,但是那时候我也还是我自己。所以我不是特别相信“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风景,自己的人生观一下就变了“那种说法。我希望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活到现在都没有过,那还要特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吗?我本来就是在东京长大的人,从中国回到日本之后也就自然而然选择了这么比较熟悉的一个城市。
我逐渐相信自己并不需要穿越山和大海,在身边也有非常有意思的人,每个人多少有比较格外的地方。那能不能把它写出一篇好看的文章?这取决于写作者的能力。如果写的文章不好看,就是我没能挖出来对方最有意思的地方。
BIE:我们常说“出格”,或许世界上有许多人特别想“出格”却被“格”拉回。您的受访者并非刻意叛逆的人,他们似乎是在“顺着生活走”中抵达了“格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另类”。
您怎么看待“主动出格”与“被动漂流”这两种状态?
吉井忍:这个好像不太能明确地分成两个状态,我们生活当中每个选择多多少少有主动和被动的一面。你选择了某一个职业,可能是你想做这个,也有可能是时代、社会状态,或者说经济状况给你的选择就这么几个。
从那些选择当中,你要选择出你觉得更中意的某一条路而已,对吧?可如果是20年前做选择,你中意的那条路肯定是跟20年后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时代或者社会的因素多多少少都有吧。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选择都有主动和被动的两面性。那么,这个里面主动的成分多还是少?只是比重的问题而已吧。
另外,还有一些偶然性,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这个纹身师三代目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他小时候在钱汤看见一个男人身上有非常华丽的纹身,他觉得很好看,受到了一种冲击,而后来他也遇见了他的师傅。
不管靠着偶然,还是其他人给的机会,一旦抓住了,就抓住不放。不一定大家都要这么干,可他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虽然他的方式不是很适合时代,尤其不一定被年轻一代认可,但我觉得仍然能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他在自己的时代当中抓住了某一样东西,并坚持了下来。或许,我们也可以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去抓住某一个机会,去面对偶然性和自己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蛮值得思考的。
吉井忍拍摄的文身师三代目雕佑西和他的工作坊
BIE:盖楼、搞笑艺人兼职垃圾清运、运营独立书店…书中受访者做的事,好像都是看起来很耗力的工作,却最终成为了持续滋养生命、催生力气的东西,让他们长出感知世界的触角,找到在世界的位置。那种“热情”到底从哪来?是起点的激情,或是在做中才慢慢生出来的?
吉井忍:所做的事情或者付出的精力最终成为一种反哺自己活下去的力量,这个状态我们不是都有吗?但可能程度不一样。
碰到了那个合适的点位,或许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热情出来,但它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一种意义。有点像夏目漱石在《我的个人主义》那本书当中说的:你没找到这个点,必须得继续找。你到最后没找到也行,但是你得不停地去找出它。
但不去找这种激发热情的点,也是个人的选择。我有个艺术家朋友,她后来选择了体制内的工作,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更重要,这也是挺好的。没有说一定要活出什么“特别的人生”。
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BIE:其实泷泽秀一那篇我特别喜欢,他有着搞笑艺人和垃圾清运公司职员的双重身份。如果在喜剧的舞台上没有表演好,他会跟自己说:没关系,我明天还要去收垃圾呢。而在收垃圾的时候,他又会想到自己喜剧艺人的这一重身份,把不愉快变成漫才的材料。他在双重的身份之间打通了不同的格子。
您是如何想到“格外”这个词的呢?
吉井忍:格子这个说法我不是特别习惯,起书名的时候我所想的“格外”是“格外好”的意思。我的受访者们已经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但仍然非常认真地面对普通的生活。这种态度反而让他们在别人的眼里变得不那么普通。
日语里面还有一个“规格外”这个说法,它通常被用来形容蔬菜水果。比如一个农家生产了一箱苹果,他们得把苹果卖给供应商。而供应商就会对蔬果的形状和色泽有一个规格的判断。不符这个规格的东西,就叫“规格外”。但这些蔬果本身味道还不错,它们本身的价值是好的,只是长得不一样而已。
怎么读也都行,“格外”可以有很多解读方式,只是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觉得泷泽秀一的活法比较值得参考,不那么固执。他想做搞笑艺人,但还接受另外一件看起来不那么体面的事情来支撑自己的生活,并且慢慢将两者发展成一种相互滋养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巧妙的状态,但这里面也有他那种比较坚韧的精神吧。
现在一个人说找不到工作,这意思通常是找不到“自己想做的工作”。其实工作的还挺多的,在日本也是。你随时都可以找到工作,只是你找到的工作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或是你认为你能做的工作,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去试一试。
这样说来,这也是跳出自己格子的一种方式吧。一直把自己放在某个格子里面,这就是焦虑的来源,其实外面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BIE:这种两份工作相互滋养的关系让我想到这几年讨论蛮多的“交叉学科”。“要当建筑师不能只干建筑”,这是书中另一位采访对象冈启辅说的话。他从盖楼跨到舞踏,最终形成一种“即兴构建”的哲学。
吉井忍:我身边有几个厨师朋友们,他们毕业后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只能做处理食材或洗碗的工作,甚至要在大厅当服务生。
这看上去和他们专业没关系,但其实怎么样分析客流?怎么样观察客人?用餐速度怎么样?今年跟食材的供应商关系如何?这些思考其实和他们的工作很有关系的。
建筑这种概念性比较强的工作就更是如此。比如说冈启辅学习了舞蹈,而且他蛮会听音乐的。你去到他所盖的那个建筑真的能感受到不一样,尤其是内部,非常活,有在某种生物肚子里面的感觉。我想,那种生命感一定和他学跳舞有关。
BIE:好像是更深刻地知道了自己在做的事是什么,这让他的专业变得更活络了。
吉井忍:可以这么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