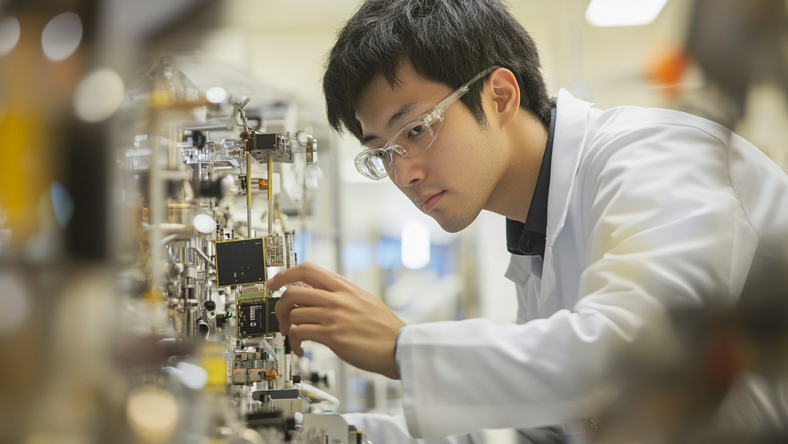【来源:虎嗅网】
“跑了这么远,就是为了能开窗”
3月22日下午4点,在郊区一个山吧和朋友聚会时,80后艺术品商人颜波感觉身体有些不妙——他开始频频打喷嚏,流鼻涕,鼻涕里甚至有血。伴随着眼睛刺痒,大脑发懵,他像意识到春天来临一样意识到:自己的过敏就要爆发了。
颜波过敏三年了,第一年过敏时他去医院检测,得知自己的过敏原是植物圆柏的花粉。春暖花开的北方是万物的盛典,于颜波却是一场劫难。今年为了躲花粉,他几乎不太出门,在家紧闭门窗,24小时开启空气净化器,还一直吃抗组胺的过敏药度日。但22号这天,他“舍命陪君子”,戴着口罩、备好药和朋友们去了当地郊区的一个湖泊,结果湖边种着不少柏树……发现中招后,颜波摸出随身携带的抗过敏药,但吃完后,他觉得“压不住了”。
当天晚上,因为过敏,颜波辗转难眠。好在他是生意人,第二天不用打卡上班,凌晨2点,他摸出手机,订了一张当天下午5点去三亚的机票。
这是他第一次去三亚,也是他第一次去外地躲过敏,“跟旅行不一样,你是被迫离开的”。他想过回内蒙老家躲躲,但老家那几天有沙尘暴。
到三亚的时候是晚上。当地气温20多度,海风里带着咸味,空气质量优。下飞机后,颜波摘掉了口罩,感觉发懵的“脑雾感”逐渐消失,整个人慢慢变得通透。
几天前,他看过网上流传的圆柏散粉视频,“像沙尘暴一样”,看得他浑身发痒。而在从三亚的机场去酒店的路上,当看到车窗外掠过的椰子树时,他感到妥妥的安全感——“没人说椰子树会过敏,对吧?”
他入住的酒店位于三亚湾,进门后,他多日以来第一次打开了窗户,“跑了这么远,就是为了能开窗”。这天晚上,自称“过敏难民”的他,在酒店睡了一个难得的好觉,一口气睡了7个小时,没有中途醒来。
对不少北方的过敏难民们来说,就近跑到天津、承德、张家口、北戴河等地躲过敏,是更加方便实惠的选择。
3月20日是一个周四,那天,设计师李铮正因为过敏濒临崩溃。他从2021年开始过敏,过敏原测出来也是圆柏花粉。3月20日那天圆柏花粉传播到达高峰期,他出现的症状与颜波类似: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奇痒,“百爪挠脸,真的想把眼珠子抠出来,打喷嚏感觉最后出来的都是血腥味”。过敏5年来,他觉得今年自己的症状是最严重的。
“设计这个工作,确实是很难走开的。但实在太难受,我受不了了。”他赶紧处理完手头工作,跟老板请了一天假,然后驱车直奔2个小时车程外的天津。
一周之前的那个周末,他刚开车去天津躲了一次圆柏花粉。当时李铮的过敏症状还算轻,车开到天津边界时,他感觉眼睛已经不太痒了。在天津,他逛了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走在老房子旁,他呼吸通畅,不打喷嚏,不流泪,“感觉活过来了”。
但这周再到天津,他的症状并没有快速缓解。他在酒店洗了一个澡,出门走了几小时,这才稍微好了一些。
有人甚至躲出了国——卞玉全家就去了新加坡。
这个三月,卞玉和丈夫都过敏了。上幼儿园的女儿看着父母在家红着眼打喷嚏,然后在困了的时候揉揉眼,说自己也过敏了,卞玉哭笑不得。
幸运的是,卞玉丈夫的公司正好需要人去新加坡办事。丈夫行程确定后,工作相对自由的卞玉请了两周无薪假,也给女儿请了两周假,准备一同前往。
但在出发前的3月20日,卞玉还是没扛住,去医院看了急诊。当时除了打喷嚏、鼻塞、呼吸困难外,她还因过敏引发了心悸。她做了心电图和血常规检查,医生安排她吸了一小时氧,开了抗过敏药氯雷他定。医生告诉她,最近过敏的人挺多的,“都是花粉过敏”。
卞玉在家休息了一天,过敏症状反反复复。在乘机去新加坡前的两个小时,她又开始严重过敏,眼睛发痒,狂打喷嚏。“再忍几个小时就好。”她对自己说。
3月24日早晨,卞玉一家三口到了新加坡。当地气温20多度,有微风,空气湿度较大。卞玉说,因为体质原因,到新加坡后,自己和丈夫的过敏症状并未立即消失,是很缓慢地一点点消失的。
还有一些资深躲过敏人士未雨绸缪,在症状出现前就选择了离开,比如季节性过敏患者王丽娟。
王丽娟是80后,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新媒体运营公司,同时还在兼职做占卜师——这两个工作基本都可以远程办公。她有过敏性鼻炎,逃离过敏的历史已经有三四年。
王丽娟很清楚自己的过敏进程:过敏前,鼻子干到冒火和生疼。一段时间后开始打喷嚏。再之后眼睛开始剧烈瘙痒。之后喷嚏越打越猛,直打到流鼻血。所以每到春天,一感觉到鼻子干,她就会像候鸟一样出门躲避。她去过上海、广州、深圳、惠州、青岛、杭州、成都、重庆等城市,一般会在外面住上一个月,等过敏季结束才回北方。
这个3月,她去了杭州——在那边,她正好有个婚姻家庭咨询师的考试。考完后她搬进了灵隐寺山脚下的一个民宿,210元一天。民宿有一个小院,她每天在周边蹓跶一圈,回来后就在小院喝咖啡,吃饭,感觉很惬意。接下来,她还会去重庆看望朋友。
“过敏的时候,你的身体很紧张,很重,”她说,“出来不过敏了,感觉状态很轻盈,心情也好了。”
“过敏患者越来越多,药效越来越差”
梅英最近看新闻才知道,自己居住的地方竟然种了400多万株柏树,这也是当地花粉的主要来源。
“我会恨圆柏。在街上看到,我会想,就是你,害得我这么难受。”梅英说。她是一个家庭主妇,最近因为父亲生病,她两次往返山东老家与现居地。在老家,她发现自己的过敏竟然慢慢好转,“幸福感很强”。从2018年过敏至今,今年是她第一次在过敏季没那么难受。
很多过敏难民到外地后,还是会本能地有圆柏阴影,会特地去看当地植物里有没有圆柏。
3月22日这个周六,轻度过敏的媒体人张依莲到承德过周末。承德的气温较低,草木还未回春,她发现避暑山庄的常绿树以松树居多,外八庙附近则有不少柏树。因为天气原因,柏树还没散粉,而她的眼睛确实也不怎么痒了。
一天之前的周五晚上,90后许静文也坐高铁到天津躲圆柏花粉。周六,她探望了一个居住在天津的好友。周日,她在酒店的投影仪上看了一场球赛,中午返程。
许静文本科学的是林业相关专业,在天津街头,她仔细观察行道树,发现圆柏非常少——另一面就是天津街头绿色不多,“挺秃的”。她本来想去参观周恩来邓颖超故居,但在网上一查,发现纪念馆往往会种很多圆柏,于是迅速打消了这个念头。
许静文的过敏史最早要追溯到2013年读高三时。当年3月,她第一次出现了持续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校医院误诊她是感冒,吃感冒药后,她一直没有好转,症状到了4月底才消失。第二年,一位医生长辈提及她应该是过敏了,在网上搜索后,许静文发现氯雷他定可以抗过敏,于是买了吃,“立竿见影就好了”。
许静文本科读的是一所全国知名的林业大学,她记得,上植物学课的时候,老师会特意提及法国梧桐,说这种树曾经在南京被大量种植,但在导致了一些过敏问题后,现在南京已经不再新种了。
“他即使说到这儿,都没有提到圆柏。”许静文说,除了上植物学课,他们还会上植物学实践课,到山区辨认植物。当时大家都觉得圆柏就是一种普通树种,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她读书的那个地区大学密布,很多大学的校园里都种了不少圆柏。许静文很喜欢逛公园,在她家附近,几乎所有公园也都种着圆柏。“那时大家对于圆柏的致敏性都没有概念。”她说。
本科毕业后,许静文在加拿大求学6年,在此期间没有出现过过敏。毕业归来,她的过敏又开始了。今年她去医院找医生开了单子,做了过敏原检测——初次过敏十多年后,她终于发现,自己的一个主要过敏原就是圆柏花粉。在临床上,过敏原检测结果分6级,她的检测结果是2级,属于中度过敏。“我觉得我已经很难熬了,其他等级更高的人肯定更难熬。”她说。
她不敢再去公园遛弯了。她感觉自己是一个行走的圆柏花粉探测仪,单位宿舍附近一个公园有很多圆柏,下班后走路锻炼,她越靠近这个公园,过敏症状就越严重。
在许静文看来,今年圆柏花粉过敏问题之所以成为热议的话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先低温、后迅速高温的天气特别适合圆柏散粉,加上北方春天气候干燥,空气中的花粉浓度瞬间增高,“过敏的人多了很多,把这个问题带出来了”。
“今年的春天来得早,过敏期提前了。”李铮说。3月初的一天,他开始打喷嚏,当时他还纳闷,这才几号,怎么就开始了,“以前我印象中,3月中旬才开始(过敏)。”
张依莲的同事中也有不少过敏的,春天公司里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抗过敏。一个和她关系要好的同事症状严重,两人会讨论该买什么护目镜、什么口罩,用什么药。另一个同事告诉她,自己过敏后想挂一家知名医院变态反应科的号,实在挂不到,只好换了另一家。
远在杭州的兼职占卜师王丽娟也感受到了过敏患者的增多——在线上,来占卜的客户有时会问她健康相关的问题,今年好几个客户跑来问她:“你说我是为什么过敏?是对花粉过敏,还是对粉尘过敏?”她建议他们直接去医院抽血化验,不要占卜,“你还是要尊重医学”。
医生往往会给患者开抗过敏药,但在许静文看来,抗过敏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她表示,市面上有三种流行的抗过敏药,分别是氯雷他定、依巴斯汀和盐酸西替利嗪。因为体质问题,后两者对她无效,而在服用氯雷他定多年后,她的身体出现了耐药性——以前她一天吃一片氯雷他定就可以正常生活,但现在,她吃完一片氯雷他定只能维持3小时。
一些过敏患者会去打抗过敏针奥马珠单抗,但许静文有些犹豫——这种针并不便宜,1200元一针,只有中重度哮喘、荨麻疹患者等少数情况能走医保。她也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自己打奥马珠单抗五六年后感觉效果递减,她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也对这种针产生耐药性,“如果那样,我以后怎么办?”
更让许静文感慨的,是网友围绕圆柏去留的争吵。这种争吵已经不再是就事论事。有人觉得过敏的人是矫情,还有人上升到了地域歧视的程度,要过敏的外地人“滚回去”。
此时,她会在留言区表明态度:“我是本地的,我也过敏。”但争吵还是在继续。
那一刻,她深深地感到,人类的悲喜有时或许并不相通。
逃离未必是最终的办法
在三亚的一天,颜波是这样度过的:白天炒股,有艺术品买卖生意时打打电话,下午3点股市收盘后出去转转,吃点东西,晚上回酒店休息。
“艺术品买卖要见人,在外面还是有影响。”他表示。但考虑到过敏问题,这一切都可以忍受。“如果不能给到让我感动的钱,我是不会回去的。”他对朋友说。他准备在海南待到4月15日,下一站是海口。
卞玉全家也准备在国外待两个星期:新加坡一个星期,马来西亚一个星期。她算了一下,到那时,这波过敏应该过去了。如果还没过去,她也有预案——利用周末去周边地区躲躲,张家口的崇礼、天津滨海新区和济南都在她考虑之列。“过敏太痛苦了,花时间、精力、金钱出来躲一躲是值得的。”她说。
周末出行的过敏难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到了工作日,他们还是得返回原地。
去天津躲过敏的那个周日中午,许静文回了家。爸爸开车去高铁站接她,上车后,她迅速戴上护目镜和口罩,没出现过敏症状。但当被爸爸从家送到单位宿舍时,她下车忘记戴口罩,在户外走了50米,她打了好几个喷嚏。过敏症状又出现了。
在天津第二次躲过敏回来几天后,李铮在半夜因过敏症状醒来。他爬起床洗脸,希望让自己舒服一点。尽管家里门窗紧闭,但他发现很难完全隔绝花粉的入侵——他家楼下就有一棵高大的柏树。
不过,他发现,短暂脱离致敏环境,对自己仍然是有很大好处的——从天津回来后的头两天,他的症状都不太明显,到第三天才开始严重,这时,再熬两天又到周末了,他又可以去外地了。
无论如何,他觉得,自己已经比不能走的人幸运了。
去杭州的前一天,王丽娟见了一个正在过敏的朋友。后者刚去医院看完过敏,一直在揉眼睛,“感觉已经是比较崩溃的状态了”。但因为工作原因,这个朋友没法暂时离开。
现在人在老家的梅英,有时会逗出不了远门的闺蜜们:“我出来躲了,你们还在煎熬。”她和这几个闺蜜约好了,如果明年春天大家走得掉,就抱团去一个城市躲过敏。
许静文说,自己闺蜜的一位同事已经带儿子回老家发展了。那个男孩过敏严重,出现了哮喘迹象,“每年都这样的话,引发哮喘会危及生命”。
当然,逃离未必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一些不走运的过敏难民发现,自己到了外地也没能躲掉。
上个周末,宝妈陈晨一家三口去了南戴河,在海边吹着海风时,她感觉自己的过敏症状好了很多。但当晚回到酒店,那种熟悉的痒痛感又出现了。次日凌晨4点,她被痒醒了。
后来她发现,酒店马路对面就有两颗圆柏,刚开始散粉。
不过,过敏难民们最近听说了一个好消息:政府已经开始全面整治圆柏花粉的问题。有的地方开始对圆柏洒水,有的地方开始对圆柏剪叶,还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实施雄株替换方案。
“希望明年不要做难民了。”许静文说。
文中李铮、梅英、许静文、卞玉、张依莲、颜波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