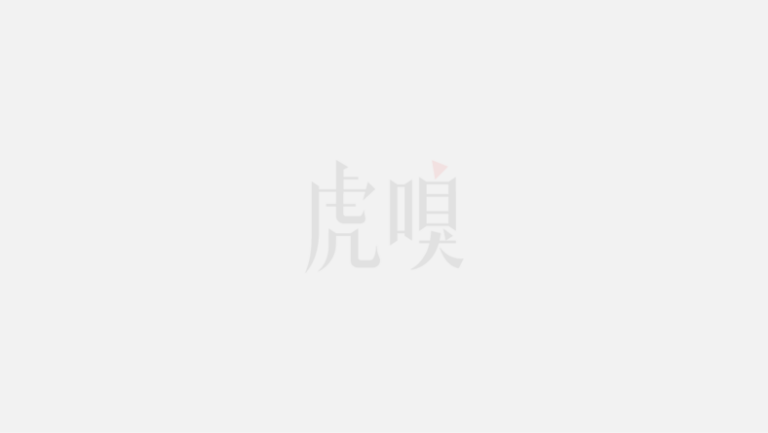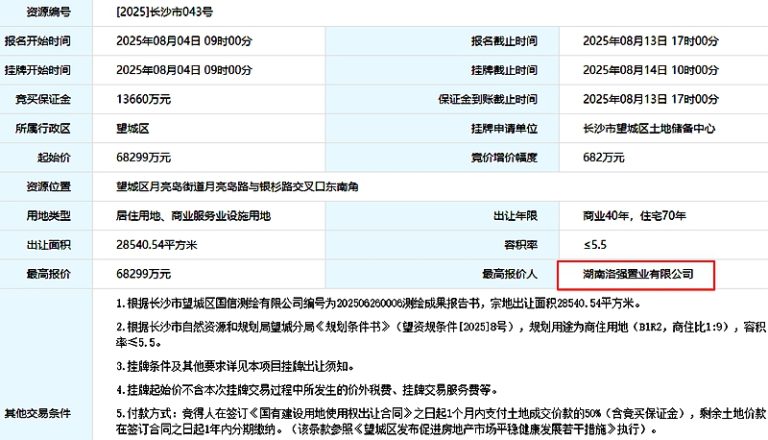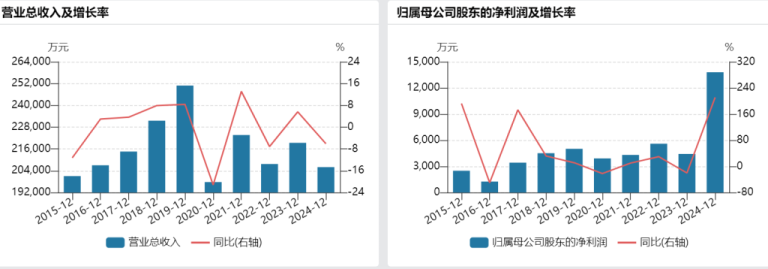【来源:虎嗅网】
周四中午,我和同事来到公司附近的饭馆吃饭。只能摆的下六张四人餐桌的小店里出奇的安静,一桌一位顾客,饭点的各不相同,用餐的姿势却几乎一致——手机摆在饭碗左边,右手时不时往嘴里扒拉一口饭,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碗旁的手机,目不转睛。
我和同事面对面坐下。各自的盖浇饭端上桌后,他掏出手机,摆在碗边,刷起了视频,时不时对着屏幕笑出声。孤独和无助的感觉席卷了我。
狭小的空间里有着一种公共场所不该有的寂静,只有后厨的锅铲接触到锅底,发出热烈的,沙沙的声响。坐在收银台后面的小孩突然哭闹起来,因为老板娘收起了他的手机。一番争执后,手机回到了小孩手里。他打开抖音,安静了下来。
没过两天,我在《大西洋月刊》上读到这样两句话:“(美国的)餐饮行业正呈现出一种‘孤独主义’倾向。人们需要更多的独处时光,社交时长再创新低。”
这篇文章名叫“The Anti Social Century”,反社交的时代。虽然文章讨论的是美国的社会现象,但在我的观察中,国内社会似乎也逐渐进入了作者口中的“反社交时代”——地铁里、马路上、饭桌前,甚至酒吧里,到处都是独处的人。他们用手机和耳机将自己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电子气泡中,有人关心着美国大选,有人和异国密友聊天,有人和乙游角色恋爱。肉体上,你我共处一室,精神上早就相隔万里。
我不太关心美国总统是谁,也无法对虚拟人物产生感情,但这也不妨碍我成为独处时代中的典型一员。我单身,无宠,为数不多的密友分散在天涯海角,一两年才能见一次面,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度过——独自居住、独自旅行、独自就餐、独自看病。
因为不喜欢所谓的“搭子文化”,我主动选择了独处,但对此又并不十分满意。我一边将“低质量的交友不如高质量的单身”这句话奉为圭臬,又一边在看到好电影而无人分享时顾影自怜,感伤自己的形单影只。
有这种矛盾,纠结心态的人不止我一个,只是当独身主义成为一种潮流时,我们不再敢承认,也不愿面对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对社交的渴望,因为孤独感成为了一种脆弱的象征,没人想脆弱。
当独处成为一种潮流
“I think she doesn’t like friendship.”在英国上学的时候,我曾听到一位德国同学和其他人这样评价我。
那是一个周五下午,几位同学商量着下课后去酒吧喝上一杯。一名来自迪拜的女生提议叫上我,他便说了这句话。
我并未感到冒犯,反而觉得他的评价像一面镜子,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一直在主动地选择独处。上大学时,别的宿舍经常集体出行,而我总是独自吃饭,独自上课。出国后我也对集体活动避之不及。我的学生宿舍里住了五个女生,共用一间厨房。我最害怕的就是下课回来后碰见其他几个人在厨房里聊天,这意味着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参与进去,聊一些自己并不关心的话题:英国的雨怎么这么多,隔壁宿舍的周末party开到多晚,竟然有男生在他们的厨房里睡了一宿,等等。甚至有几次,我走到门口听到室友们在餐厅里聊得火热,为了避免参与,我蹑手蹑脚地下楼,跑到图书馆自习去了。
旅游时,我也只会和关系最亲密的人一起(作者供图)
如果说当年我所处的社会还在将“拒绝social”视为一种负面行为,那么几年后的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The Anti Social Century”的作者Derek Thompson称,主动地选择独处,已经成为21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社会现象。
外网有几个流行的短视频和表情包,生动表达了网友对出门社交的躲避,和对独处的依赖。
—朋友:“周末出去玩吗?”
—我:“不了,我周末有很多安排。”
—我实际的安排:躺在床上躺一整天。
有宠物的人可能更喜欢这个:
—朋友:“出来吃饭吗?”
—我:“不了,我现在脱不开身——我的猫正躺在我的脚上睡觉呢,我走不开。”
听起来有点好笑和可爱,但仔细想想,这种描写并不夸张。流行的表情包总能精准表达时代情绪。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独处的渴望已经超过了对他人的好奇,以及对面对面沟通的需求——这不是一种猜测。今年1月,《三联生活周刊》专门制作了一条视频,直指当代年轻人的核心疑问:我为什么要跟人交往?
如果说表情包只是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那么在网络红人的包装和社交媒体的传播下,“独处”已经在年轻群体中演化为一种看似积极的生活态度,一种值得追随的潮流趋势。这一点在国内,尤其在所谓的“高知青年”群体中同样适用。
在国内,最流行的独处方式是独居和单身。“30岁以上,单身,独居,无社交”是常见的vlog文案开头。自我介绍里,博主们大多将自己定义为那个人群中格格不入的角色。视频里,他们从容地起床、护肤、做早餐、磨咖啡、运动、学习、阅读、陪宠物玩耍,整个视频里很少出现第二个人,也没什么社交的场景。
那些谈论独处的博主们大多将自由、独立、自爱视为独处的最大意义。没有他者的干涉,我们似乎可以尽情地成为自己,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生。《瓦尔登湖》是他们常常引用,以佐证自己观点的书籍:“一个人如果熬到没人联系,没有饭局,没有社交,那要恭喜你,可以尽情地去享受孤独。”
抗拒恋爱与婚姻在国内年轻人之间越来越主流。或许是看多了老一辈夫妻之间性别地位不平等,或者缺乏沟通的相处模式,对于爱情和婚姻之中存在的妥协与不公,我们丝毫不想忍耐也不愿妥协。爱情之中最难以用理性衡量的激情,被我们称之为“上头”。感情似乎成了一件稳亏不赚的事,我们不接受这种情况的发生。
当“不需要认同,不需要干涉,不需要爱情”成为主流,我的孤独开始变得难以启齿。朋友们经常把“不谈恋爱破事没有”挂在嘴边。每次我提到自己很想谈恋爱,他们都会教育我“先爱自己”。渐渐的,我对独处带来的孤独感闭口不谈,装作自己十分满意。我清楚地感受到,我活在一个提倡个人主义的环境里,情感需求,尤其是爱情需求被视为一种弱势的象征,而我不想被视为弱者。
宠物博主“妈耶是只猫”在小红书上说,虽然养猫可以让长期的独居生活更充实,但他在带猫逛花店时还是想“买点玫瑰送个人”,在工作疲惫时还是想有个人能抱抱自己。一个长期独处的人渴望人际关系与互动,对此我感同身受。
显然,对独处感到孤独的不止我一个人。豆瓣上有一个九万多人组成的“社交能力复健小组”,组员被称为“社交低能儿”。这里充满了与博主们“渴望孤独”不同的声音:每天都有八九个人发帖,倾诉着的苦闷:孤独,甚至沟通能力下降。
“我想要有人跟我说说话。”
“一个人待久了,连正常的闲聊也不太会了。”
“因为物理距离+三观裂隙,失去了曾经的好友,深知步入社会后,大家都没有太多的耐心和精力和新人建立深刻的友谊。”
“渴望深度友谊,但只找得到一次性搭子。”
他们渴望社交——有人渴求单纯的陪伴,有人想要灵魂的共鸣。
我们为何选择独处,又为何不满
和我一样,安琪(化名)也在独处与孤独之间拉扯,矛盾着。安琪三十岁,生活在国内的新一线城市,从事于教育行业,周末和节假日都要上班。
特殊的工作时间本就缩小了她的社交范围,在休息时间,她依然选择独处,因为不喜欢“消费型的,无用的社交”。
“和同事约饭、狼人杀、KTV,甚至逛街购物聊天。”安琪和我列举到。
称之为“无用”,是因为安琪无法从这些活动与交流中获得情绪共鸣,或者更有价值的信息:“人均一两百块钱,一天嘻嘻哈哈下来,除了获得消费性质的体验,就是三五个熟人不断重复自己一成不变的价值观,或者讨论一些没有营养的内容——电影、明星、八卦、旅游。”她无法从中获得真正的陪伴感。
出于这些原因,休息时间她也很少出门,而是在家看书、健身、睡觉、冥想、做饭。大部分时间她都怡然自得,但有时刷到有趣的内容,想与人分享,或者交换看法时,她发现能与之产生真正交流的人其实很少。
安琪的孤独感并非来自独处本身,而是来自于一种不被理解或接纳的处境。三年前,因为健康问题,安琪开始践行生酮饮食。她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吃碳水,每天至少运动半小时。身边人不理解,也不认同。结婚前,她向丈夫索要彩礼的行为也受到了大部分人的非议,认为这有损道德形象。
“在他们眼里,要彩礼等于卖女儿。我是所谓的独立女性,所以不应该要彩礼。”安琪解释道。
起初,她还不断和身边人解释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想法,甚至试图劝说家人和她一起尝试这种生活方式。但久而久之,她感觉自己在白费口舌。
“人们只会相信自己已经相信的东西。”安琪说。
在彩礼的事上,母亲是最反对的,为此她们争吵过,安琪感到很无力——母亲明明应该是最支持自己的人,此刻却最反对她。对此,她似乎很失望:“我想把我的经历分享给我最在意的人,而他们的不理解,甚至对我的逃避,最让我感到孤独。”
线上社交解决了孤独,还是推动了孤独?
我们几乎可以确认的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发展推动了现代人的独处。但是“The Anti Social Century”的作者Derek Thompson敏锐地观察到,人与手机深度绑定的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人们的独处时光变得十分拥挤,而在集体中却显得更加孤独。
这就像我在公司附近吃午饭的那个中午。我与近十个人共处一室,除了点菜和结账,二十多平米的屋里几乎没有一点对话和互动。我试图和同事聊天,但他正带着耳机看美剧,没听到我说话。
独处时光的拥挤——不难理解——源自网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总是碰见志同道合的人,获得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但当你来到线上,这些都不再是问题,社交媒体甚至会将你可能感兴趣的人、事、物推到你眼前。在中国近11亿网民中,平均每人每日的上网时长已经达到了5小时37分钟(国家统计局),约占清醒时间的33%。按照八小时工作制计算,我们业余时间的61%都在上网。
当安琪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交流充满了无力感,就开始将目光转向线上,试图在自己喜欢的公众号,博主群等线上组织中,与和自己类似的人“抱团取暖”。刷帖和评论成为了安琪解决孤独感的方法,她每天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都在使用社交媒体,早晨醒来和晚上睡前都会刷上半小时左右。
“网络一线牵,珍惜这段缘。”当时间,场域和物理距离都不再是问题,“陪伴”的成本似乎更低了,因为它不需要通过友情或者爱情来实现,也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来维护。2024年,“无声连麦”的话题在社交软件Soul上获得了75.5万人的参与,8亿次浏览。Soul与复旦大学联合发布的《2025社交报告趋势》如此描述这种现象:“如果说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让每个人几乎变成了一座孤岛,那么无声连麦另一端的陪伴就是在反复告诉你说,你并不孤独。”
手机和网络及其衍生品,看似是人类面对“孤独感”给出的解决方案,但Thompson指出了背后的问题:适当的孤独是一种健康的情感反应,它提醒人们,是时候离开沙发,走到外面,和他人产生互动了。但问题在于,如今美国大多数人在面对孤独感时,不再会做出这种反应了,反而将“逃避社交”视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默认选项,造就了“在集体中显得更加孤独”的社会现象。
“我孤独,焦虑又疲惫,幸好我取消了原本的计划。”Thompson如此概括当代人的心理状况。
这有点反生物学,也有点拧巴。安琪也承认,她试图从线上社交缓解孤独感的行为如同隔靴搔痒,人与人之间的绑定还是要通过面对面,甚至肢体接触来实现。大多数朋友都不在身边的我早就成为了社交软件和网络的重度用户,但是止步于线上的交流,单方面的信息输入和输出,都让我的现实生活变得没有根基。
“肉体生活在线下世界,但是精神却生活在线上,这是一件很割裂的事情。”安琪说道。
Thompson将之归咎于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相比真人社交,被电视、网络、社交媒体“武装”起来的独处环境更可控,更便利,从而成为我们消遣的“捷径”——既然有更方便的途径来消磨时间,为何还要冒着被冒犯,被抛弃等风险交朋友?另一方面,网络在不知不觉中向我们输入了过量的信息,使我们出现一种现实层面依然孤独,精神世界却早已疲惫的割裂感。正是这种割裂感让我们主动选择独处,又对此感到不满。
“我已经退化到没有能力花费长期的精力,维护更多的社会关系了。”安琪告诉我。
线上社交是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孤独?还是加重了我们的孤独感?早在1998年,就有研究发现,在人们刚开始使用网络的1-2年里,快乐感和社会连接感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使用网络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最大 。在美国,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情绪已经达到历史新高(Thompson)。在国内,从双相情感障碍到ADHD,网友对心理健康疾病的关注,甚至自我确诊的情况也越来越常见。
“社交贫乏的童年几乎必然导致社交滞后的成年。”这是Thompson的观点。根据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人类在童年时期需要与其他孩子一起,不受监督地互动,在测试自己能力极限的同时学会管理冲突,忍受痛苦。
可见,当网络侵占了儿童与同龄人互动的时间,其社交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如今已不局限于儿童,在整个社会中都能看到影子。社交媒体上,冲突与对立时刻都在上演。视频的弹幕中总有争吵,微博的评论里总有攻击。黑人女性Halle Bailey主演的电影《小美人鱼》上映时,我在一条微博下发表评论,认为主演的长相并没有那么丑,因此受到了许多攻击,甚至有人说“希望你全家都长这样”。
当我们习惯于在网上选择性地查找,倾听自己喜欢的声音,突然回到线下,发现真实世界的不可控因素如此之多,就会变得异常不适应。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夏莹曾指出,移动社交加重了我们对非确定性的恐惧。易怒,难以处理冲突,这些情况都在我身边真实发生着。我们面对,接受和处理“差异”的能力,正在逐渐退化,这也是导致我们孤独感的重要原因——建立关系是人的天然需求,但在一段稳定的,能解决孤独感的关系中,差异和冲突必然存在,我们必须面对。
“重建附近”,应该如何实践?
“我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人。”“(我)习惯并且享受这种独立。”在《三联生活周刊》发布的视频“当代年轻人的疑问:我为什么要跟人交往?”中,一位男生这样评价自己。
无论是他,安琪还是我,我们似乎认为自己只需要“深度”的情感链接,也不需要太多朋友。但至少对于我来说,追寻了七年时间,理想的社交状态在我身上依然没有彻底实现。每结交一个好友,没过多久,我们就会因为各种原因分开:有时她离开,有时我离开,总的来说,因为我们都有各自的梦想要追寻。
在与《当代青年研究》的对谈中,人类学家项飙曾提出,现代社会中,空间逻辑消失了,时间逻辑取而代之。除此之外,他还观察到,当代年轻人过于关注两极,即自我和远方,并因此产生很大的情绪波动。这些宏大叙事是通过各种抽象的说法形成的,也是人们产生情绪波动的原因。而“重建附近”,关注自己周边的,具体的生活,是他针对当代青年的焦虑提出的解决办法。而孤独感作为焦虑的来源之一,也可以通过重建附近来解决。
意识到这一点,是从我家的一次马桶漏水开始的。刚搬到上海工作时,我在临街的独栋老楼里租到一个狭小闭塞的“亭子间”,入住几周后才发现,因为二房东的私自改造,加上老楼本就年久失修的管道,我家的下水道经常堵塞,漏到楼下临街店铺的门前。
一天,我家的马桶从早上就开始沿着地砖往外渗水,难闻的味道充斥着整间厕所。楼下卖古玩字画的老板又敲开我家的门,说我的厕所漏水,滴到了他的店前,差点滴到他的字画上。
我给二房东打电话,他推脱给居委会和市政,在我的坚持下才说自己不在上海,叫来了一位朋友给我解决问题。
这位“朋友”不情愿地来到我家,言语粗鲁,态度强硬,我们大吵了一架。
问题解决后,我还在气头上,楼下的老板突然问我:“小姑娘,你是不是搞音乐的?”
我被他突如其来的问题搞得摸不着头脑。他的字画差点被滴上下水管道里的水,我以为他会生气,而且是生我的气。但他看起来似乎毫不在意,心情依然很好。
“我看你这一头卷发,还以为你是唱摇滚的呢。”他笑着跟我聊起天,同情我们这些身无分文,搬到上海奋斗的年轻人,还要受二房东的欺负。
说来搞笑,水管漏水的麻烦事还让我结识了楼下卖皮具的苏南大哥,和古玩店老板聊天时我又认识了在隔壁开店的,卖出口手工艺品的同龄女孩,还有她做旗袍的舅舅。他们的店都开在我家楼下,彼此相邻。
苏南大哥和古玩店老板都是我家水管漏水的受害者(虽然我也是),但他们从未因此责怪过我,反而在我每次回家或者上班路过的时候打声招呼,偶尔问问我的工作,聊一聊这片街区的历史,聊聊他们是怎么在上海立住脚的。
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就像我知道他是古玩店老板一样,他知道我在媒体行业工作。但有了这些随机的,友好的“弱关系”,我立刻不再感到自己在上海是孤身一人了。后来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外出吃饭,在家门口的十字路口,古玩店老板老远就看见了我,一边招手,一边喊着“记者!记者!”想要叫住我和我说话。
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被看见的感觉,也觉得自己“融入”了上海,融入了生活。也是那时开始,我才理解“重建附近”的意义。《三联》的视频里,不止一位大学生说道,如果别人想和ta建立关系——恋爱关系也好,朋友关系也罢——ta会首先考虑这个人是否会给他带来负担。这佐证了项飙的观点:如今的城市生活功能性过剩,生态性不足,导致了年轻人孤独无援的感受,以及对线上世界的依赖。
他提到,这种现象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夫妻之间,一方拿自己的爱人和别人作比较。在做这种假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忽视了人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将目光聚集到他所处角色的功能性上,比如赚多少钱、有没有更好的工作、能否让更多人羡慕。
“当你把自己的生活当作一个生态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身边的一切人,一切事都是可以被替代的。”项飙说道。
而在我看来,具体的实践办法就是主动与真实社会建立联系——了解你身边的人,看到他们的故事,与他们产生互动,寻找更多理性和公平之外的,情感上的感受。
后来,每一次搬家我都会开始主动认识身边的人:隔壁邻居,咖啡店员工,办公楼的保安和保洁。互动通常从见面时的一个微笑和“你好”开始,慢慢地,邻居的阿姨开始夸奖我养的小猫。封控时,我领到了多余的蔬菜,送给了邻居。第二天,阿姨敲开我的房门,把做好的焖饭分给了我一碗,用了我给她的胡萝卜,黄瓜和洋葱,上面还盖着两个煎鸡蛋。
邻居分给我的饭(作者供图)
有了这些鲜活的,充满情感的互动,我的生活变得具体起来。在我的记忆里,楼下的商户不再是“楼下的商户”,邻居也不再是“邻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以及我们之间的故事。
“不要因为即将离开而封闭自己,不要害怕分离。你永远不知道你今天结交的朋友,下一次会在哪里遇见。说不定我将来会去中国看你呢。”这是我在英国认识的朋友对我说过的话。认识她的时候,我还有十几天就要回国了。
网络的存在,信息的流通让我们获得了更多机会,看到更多可能性。那些和我有类似心境和纠结的人在找到理想的生活方式之前,可能还会不断地离开一个地方,离开一群朋友。但我们必须要承认,再理想的生活方式都会有遗憾和不完美。如果说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孤独是必须要付出的妥协,对身边人多一点热情与好奇,少一点对所谓“公平”和“回报”的计较,或许就是我们对抗孤独的出路之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观廿,作者:Jacq,编辑:黄粟